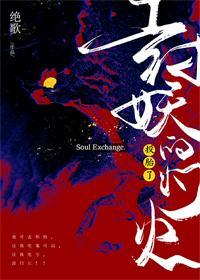69书吧>民国人物传记蔡元培 > 第58页(第1页)
第58页(第1页)
的确,以前的人提倡白话,是为引车卖浆者流说法,是要去“启”
别人的“蒙”
。启蒙者自身,既然不“蒙”
,自然可不用白话。所以一般的士大夫,完全可以置之不理。那被“启”
的“蒙者”
一边,自己是否承认被“蒙”
,或其承认的“蒙”
是怎样一种“蒙”
(很可能只承认不识字而被“蒙”
却并非是不知知识那样的“蒙”
),及其是否想要或愿意其“蒙”
被“启”
,恐怕都是要打个很大的问号的。但这不是我们这里能讨论的问题。[27]今胡适所倡导的白话,是为士大夫自身说法,是要“启蒙”
者先启自己的“蒙”
,这就与以前有根本的区别了。可以做古文的士大夫自己,包括留学生,当然不会赞成;后者尤其反对得厉害。正因为如此,胡适的白话文主张在美国留学生圈内才几乎完全得不到支持。后来文学革命以及文化运动最有力的反对者,仍是留学生,这一点后面还要论及。
另一方面,民国初年那些介于上层读书人和不识字者之间的边缘知识青年,当然就要拥护白话文运动了。前引陈独秀所说的文学革命社会背景,若仔细观察,实际上就只限于向往变成精英的城镇边缘知识青年或知识青年,真正通俗小说(未必白话)的读者群是不同的(详后)。民国初年的中国有一班不中不西,中学和西学的训练都不够系统,但又初通文墨、能读报纸之辈,因科举的废除已不能居乡村走耕读仕进之路,在城市又缺乏“上进”
甚至谋生的本领,既不能为桐城之文、同光之诗而为遗老所容纳,又不会做“八行书”
以进入衙门或做漂亮骈文以为军阀起草通电,更无资本和学力去修习西人的“蟹行文字”
从而进入留学精英群体,但其对社会承认的期望却不比上述任何一类人差。他们身处兴的城市与衰落的乡村以及精英与大众之间,两头不沾边也两头都不能认同——实际上当然希望认同于城市和精英一边而不太为其所接受。
从基层奋斗到上层的胡适是非常理解这种希望走近上层社会的心态的。他在后来写的《中国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的“导言”
中说:“小孩子学一种文字,是为他们长大时用的;他们若知道社会的‘上等人’全瞧不起那种文字,全不用那种文字来著书立说,也不用那种文字来求功名富贵,他们决不肯去学,他们学了就永远走不进‘上等’社会了!”
[28]像孔子一样,胡适希望能够向学的人都有走进上等社会的机会,所以他特别注重教育与社会需求的关联。他刚从美国回来时就注意到:“如今中学堂毕业的人才,高又高不得,低又低不得,竟成了一种无能的游民。这都由于学校里所教的功课,和社会上的需要毫无关涉。”
[29]且不管胡适所说的原因是否对,城市社会对此类中学生的需要有限是事实。
胡适写那篇文章的口气,似乎尚未有意识地把这些人当作“我们”
看待。其实他们才真是最支持白话文运动的“我们”
。这些人在穷愁潦倒之际忽闻有人提倡上流人也要做那白话文,恰是他们可以有能力与旧上层精英竞争者。胡适明确指出,文学革命就是要把“大众所酷好的小说,升高到它们在中国活文学史上应有的地位”
。小说的地位升高,看小说的“大众”
的地位当然也跟着升高。胡适并有意识地“告诉青年朋友们,说他们早已掌握了国语。这国语简单到不用教就可学会的程度”
。因为“白话文是有文法的,但是这文法却简单、有理智而合乎逻辑,根本不受一般文法转弯抹角的限制”
(这已与其《文学改良刍议》的第三条矛盾了),完全“可以无师自通”
。简言之,“学习白话文就根本不需要什么进学校拜老师的。”
实际上,“我们只要有勇气,我们就可以使用它了”
。[3o]
这等于就是说,一个人只要会写字并且胆子大就能作文。边缘知识青年一夜之间不降丝毫自尊就可跃居“上流”
,得来全不费工夫,怎么会不欢欣鼓舞而全力支持拥护!到五四运动起,小报小刊陡增,其作者和读者大致都是这一社会阶层的人。从社会的层面看,报刊不也是就业机会吗?他们实际上是自己给自己创造出了“社会的需要”
,白话文运动对这些人有多么要紧,而他们的支持拥护会有多么积极,都可以不言而喻了。
胡适的主张既然适应了民国初年社会变动产生出的这一大批边缘知识青年的需要,更因为反对支持的两边都热烈参与投入,其能够一呼百应(反对也是应)、不胫而走,就不足为奇了。而且,如前所述,胡适写文章是有心栽花。他“抱定一个宗旨,做文字必须要叫人懂得”
,为此而改了又改,就是“要为读者着想”
。胡适关怀的不止是他自己是否懂,而且有意学梁启,“要读者跟我的思虑走”
。努力使他的文章“明白清楚”
的结果是“浅显”
,而浅显又适应了边缘知识青年的需要。同时,他作文既然不是“只管自己的思想去写”
,而是“处处为读者着想”
,有时或不免因为想象中的读者的缘故要收束或张大“自己的思想”
,这或者使胡适所表述的未必总是完全代表他的本意(应至少代表了大意)。但这样与别人不同的一心一意从读者角度出的苦心,在民初思想接收者渐居主动地位时,就给胡适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正面回馈。
同时,白话文运动的迅成功也还有另外的非思想的原因,那就是胡适和陈独秀这两个安徽老白话作家的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