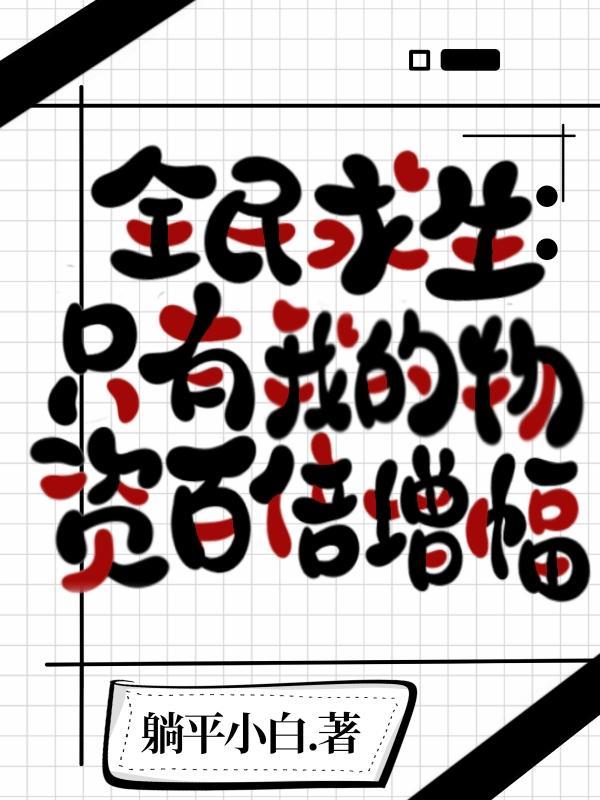69书吧>阿奴诺比交易最新消息 > 第七十三节 索玛报复(第1页)
第七十三节 索玛报复(第1页)
刘仲与阿奴两人张口结舌,现在他们就是人家砧板上的肉,刘畅爱怎么切就怎么切,剁碎了都行,不要说主婚,命都在他手里。阿奴连忙示意阿宝去找沈青娘等人,手上恼恨的狠狠拧着刘仲腰上的肉,刘仲吃痛又不敢叫出来,脸上表情瞬息万变。
刘畅误会了。当年他也不确定是否能够成事,有心向沈家之类的世家大族示好,所以放沈谦与刘仲离开。现在与刘鹏对峙数年,钱粮兵士消耗巨大,双方都开始力不从心。他隐隐约约感觉到刘鹏锲而不舍追杀刘仲的原因绝对与早逝的皇帝有关,如果能够破解谜团,应该可以给他致命一击,尽快结束这种‘绞肉机’式的对峙。如果破解不出,有刘仲站在他的阵营里现身说法,刘鹏杀妻灭子残害师尊的行为证据确凿,也将为世人唾弃,扭转自己因为乌蛮叛变而不利的舆论局面。最近几日试探刘仲,他说话虽然恭敬,言语间却推三堵四不肯归附自己。本来他就对沈家滑不留手阳奉阴违的态度很恼火,现在见刘仲一副要哭出来的模样,又想起最初沈谦那句‘不敢附逆’,心中恶念横生。他明是勤王暗是造反,这种人的心理一向是做了婊子还要立个牌坊,最忌别人说这些。当下阴着脸问道:“在你心里,九叔就这么不堪,连给你主婚都不配?”
“不是。”
见他脸上杀气隐隐,刘仲急得额头冒汗,现在谁敢对这个手握重兵的土皇帝有意见。
沈青娘在门外说道:“郡王爷,阿仲憨傻,有什么说错的地方,你别往心里去。”
沈家几个人都走进来,后面跟着阿宝,阿奴松口气。
刘畅冷哼一声,脸色缓下来,口气却不容置疑:“准备一下,过几日就成亲吧,阿仲也十六岁了。”
沈青娘的脸色比他更难看:“郡王爷,你把阿仲当成什么了,虽说梁王不慈,但是阿仲的世子身份还在,哪一个宗室子弟能这样草率成亲?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这些仪式,哪里是区区几日就可以做完的?况且还要上告宗庙,请司天监选定吉日。”
那可就远了,宗庙在长安。
刘畅语塞,他一开始只是存了恶作剧的心理,还真没想过阿仲的身份,不由得有些歉然。
气氛一时僵住,沈青娘又胡诌道:“阿奴是吐蕃山南王的侄孙女,身份贵重,吐蕃王族嫁女规矩多如牛毛,这般草率,将致阿奴与何地?难道让她做妾不成?让山南王知道我们如此薄待阿奴,只怕会找我们算忘恩负义的帐。”
刘畅奇道:“你们是被山南王收留的?”
“不是,是他的哥哥。”
沈青娘把阿波扯进来,既然刘畅与山南王存在合作关系,看在这个份上他大概会对阿奴客气些,不计较当年的事情。反正阿波也是货真价实的山南王表哥,看那支吐蕃商队对他毕恭毕敬,也不怕戳穿。
刘畅迟疑,沈青娘只好又在他耳边嘀咕了一句,刘畅奇怪的瞄了一眼阿奴的身材,这时候一个侍女来报,索玛王妃来了。刘畅借驴下坡,连忙走了。
“青姨,你比我还能胡诌。“阿奴好笑,青姨也学坏了。她好奇问道:“你最后跟他说什么?”
沈青娘吞吞吐吐:“不过,不过是说你的月信没来,大汉婚律,女子月信未至不可成婚。”
一句话说的阿奴脸如红霞,这种事情被说出来公然议论,她脸皮再厚也吃不消,顾不得螃蟹,一溜烟走了,差点和闻讯赶来的云丹撞个满怀。
身后沈谦叹道:“那已经是老黄历了,不过是太祖当年看见幼女成婚生子往往夭折,一尸两命的事情常有生,才规定女子未满十六岁,月信未至不可成婚,但是十六岁的女子大都来了月信,所以现在也没人注意这个,难为你想出来敷衍那刘畅。”
&1t;aid="zsy"href="《仙木奇缘》&1t;a>
沈青娘道:“哪里是我敷衍,真是如此。”
一屋子男人齐齐红了脸。
接下来几天,阿奴不好意思出房门,连螃蟹也是沈青娘与阿宝送进来给她,不过大闸蟹可能长途跋涉太过劳累,她吃起来总觉得不如记忆里的美味,啃了两只也就算了。
索玛一进来就皱了皱眉头,一屋子螃蟹味,阿奴见到她扑上来搂着她的脖子高兴的大叫,还朝她呼了口气,熏得她跳出门外:“你们怎么都爱吃这种腥臊难闻的东西。”
阿奴乐得‘咯咯’直笑,欺负不了刘畅,作弄他老婆也可以愉悦身心。
但是索玛是有事而来,她不肯进来,两人就坐在院子里敲定了合作参股建立马帮的事情,这是阿错与索玛已经谈过的,现在不过补充一些细节罢了。双方都很满意,乌蛮与吐蕃人关系紧张,有了阿奴的保证他们的马帮路线可以延伸的更远,而阿奴的马帮可以从乌蛮直接进入大理乃至缅甸。至于中原,阿奴依仗与沈谦的合作关系给索玛画了个大饼。刘畅与乌蛮撕破脸后,边境关系一度紧张,不过刘畅分不出兵力对付,就这么不尴不尬的拖着,现在忽然示好,大概力有不逮,害怕腹背受敌。乌蛮人的马帮已经进入不了中原,生意大受影响,见到阿奴规划的美好远景,提的条件也很优惠,索玛大喜过望,一口答应,没有注意到阿奴所说都是一种假设,她还没时间和沈谦谈呢。她们也不用签合约,口头说了就算。那种东西是对付沈谦之流的奸商的。阿奴始终无法全心信任汉族商人,这也许是自己心思诡诈的缘故,她像根香蕉似的里外不同,内心里实打实的是个汉人。
阿奴见索玛不过二十出头,已经一脸的疲惫,眼角都有了鱼尾纹,以前那个鲜艳明媚的少女变成了残花般暮气沉沉的少妇。这就是政治婚姻的危险,难保枕边人一朝反目,倒戈相向。她心中酸冷,低声问道:“姐姐,你后悔么?”
“不知道呢。”
索玛怅然半晌。
两人一时无语。从人早已被屏退,院子里静悄悄的,只有枫叶不断掉落的‘簌簌‘声,阿奴不让人清理,红叶像一匹灿烂的红锦般铺了满满一地。
“原来不打扫也有不打扫的好处。”
索玛轻声说道,好像声音大了就会吹跑这些美丽的叶子似的。
阿奴趁机提出来:“听说州秋天风景极美,姐姐,你给那个王爷吹吹枕头风,放我们出去玩玩吧,都关了快一个月了。”
索玛奇怪:“你们是被关起来的?”
“对啊。”
阿奴点头如捣蒜,一脸苦相。
“为什么?对了,阿错不是说你嫁给了阿岩,刘畅怎么说你跟他侄儿有婚约,他们是不是逼你成亲?他的那个侄儿脸上那么大一块疤,哪配得上你,刚才还把阿合吓得直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