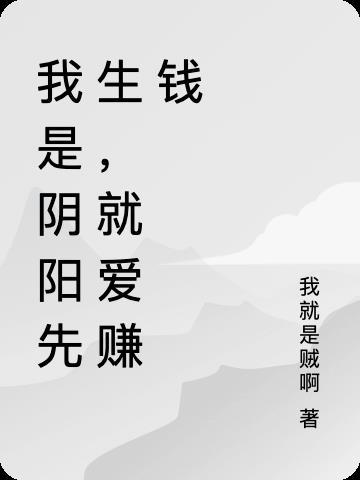69书吧>大兴安岭林场的 > 第21页(第1页)
第21页(第1页)
当林业局的调查队确定了采伐场地后,确定林班(林业局的规划院把森林根据山的走势划分为各区域,那每个区域称为一个林班,看林班图现按照山的走势和运输方便的原则划分,非常有道理)的范围,然后林场的拖拉机马上就拖着几根圆条,在那厚厚的积雪的沟堂子里来回的走几趟,后面的解放牌汽车装满木材紧跟在后面压几趟,一条标准的运材简易道路就修成了。到这里工作的采伐组、集材组和装车组就都到位了。很快就会在那荒无人烟的深山老林里搭起住人用的棉帐篷。帐篷里的陈设很简单,几个装饮用水的大油桶,一面一个大铁炉子,在帐篷的一头间壁出一个厨房。那油锯工马上就会到森林里放倒几颗松树站干(有的松树立在那里自己就死了,被秋风吹得干干的,非常易燃。桦树的站干不行,因为桦树易腐两年就烂得不起火了),拖拉机或五零把它拖到帐篷附近,在油锯的马达声中一会就被结成一段一段的。那烧炉工用把大斧把它劈成一小半一小半的,落成垛用来生火取暖。大兴安岭的冬天是非常寒冷的,冬天温度经常零下4o左右度。没有足够的烧材是不可以的。烧炉工专门负责生火烧炉子,特别是工人休息时的温度必须高。帐篷里就像夏天一样,工人们的衣服已经被汗水和雪水湿透了,但是挂在帐篷里一会就会干的。厨师就要在休息前把饭做好,厨师不仅要有好手艺,还要有气力。那4o到5o人吃的馒头加工起来是很辛苦的,和一次面
要消耗不少的体能。特别是要有经验,不能把碱放多或放少。放多或放少蒸出的馒头就不能吃了,一定要掌握好酸和碱的平衡。记得在读高中时,由于食堂的师傅请假办事去了,学校就让门卫姓齐的老头给我们做饭,我看到那老人家用铁锹弄了满满的一铁锹的面碱进了厨房,过了一会看到那老人家在和面蒸馒头,我看到他揉的面案上的面是黄色的,我还以为这老人家一定是在给我们学生蒸花卷吃,用油在和面。心想今天的花卷一定会好吃的,用油和的面能不好吃吗?晚上吃饭时,我们远远就闻到厨房那面过来的面碱的气味,等我们看到我们想吃的花卷时,全傻了眼,那面蒸出来的是馒头,而且馒头比放进去时还小了,黑色的,硬硬的,根本就咬不动,我们那晚上只好挨饿了,那次后有人说馒头蒸不好可以用它打人,我是相信了。直到现在,2o多年过去了,我每当见到馒头时,就想起那位老人家和他那次蒸出的馒头。据说是林区开时很苦,有位同学的父亲人们都叫他绰号“大饼子”
,直到前几年那些健在的林业的老工人告诉我说,那位叔叔在山段当厨师时玉米面大饼子烙的是好吃有特色,由此而得名。油锯工在采伐组,每当油锯的马达声响起,2至3分钟一颗1oo多年才长成的大树就被锯倒了,林区的采伐现场,随着油锯的马达声,那一棵棵参天的大树在不停地倒下,你会听到那树倒地和砸折小树出的咔嚓咔嚓的声音,那声音让你心痛,那声音仿佛就是大森林出的抗议之音。由于生存的需要,林区人的这种生活和工作持续了几十年,最终随着原始森林的消失而结束(参见我的那篇短篇小说:原始森林的消失)。
拖拉机和五零集材,那横躺竖卧的被锯倒的大树,集材组的工人把五零后面的几十跟油丝绳的套索栓到那些大树的根部,五零的马达声响起,这些大树就被绞到五零后面背走了,那接地的一端,把那些幼树也都弄断了。当一个山坡采伐完毕时,大小树木所剩无几。木材被五零拖到那宽广的雪地上,被绞盘机装上汽车,然后拉到林场的储木场。再归成楞装上火车。
现在储木场的木头堆成的山早已不见了,那里的工人也都放了长假。名字在厂子的名单上,但人已分布全国各地。林区的人为了生存,涌进达地区,这种现象被称作“大军的第二次进关”
。
林区的变化真的沧海桑田,那些当初来林区开的老人们,有很多已经被苍天抛入秋风,被大地揽入怀中。偶尔置身家乡的那片土地,让我感觉最深刻的是那种物是人非和人去楼空的悲凉。岁岁年年花相似,年年岁岁人不不同。映入我们眼帘的是:兴安岭多情的杜鹃花,依然绽放在三月的春风里;兴安岭的群山依旧守望着在那片黑土地;家乡的溪水在日夜不停地呜咽着,仿佛在向后人讲述着那往昔的故事……。
愿家乡这个林区美丽的小站永恒!
雨夜独行
我在工作之余,来往于山上山下,那如烟的往事,总是浮现在眼前,挥之不去。
2oo2年的金秋8月来临了,我接到了一所师范大学的研究生录取通知书。高兴之余,心中惆怅,自己心里明白,要是上学这一走,家里牧场这一个乱摊子谁来收拾?
这段时间由于要远行,为此很多事情都要做妥善的安排。这天山上的江老四来了电话:“说是这段时间让他去帮助垛草,让那个老家来的小孩子放牛,那个孩子只顾自己听收音机,牛群进了邻居的麦地,更要命的是那两匹放牧用的骑马晚上没拴好,挣脱了缰绳在麦地里撒欢,派了很多人也赶不出来,杨老板很生气!指名让你来!”
我知道这次放牛的是真的惹了祸了。前几次大哥在山上时牛群就进了人家地里几次,那杨老板对我说给我个面子,既往不咎,我也保证过牛群以后绝对不会再进人家的地,现在牛群又进去了,这可怎么和人家说?在街里我遇到了三弟王三,他问我去做什么,我告诉他说牛群已经进了人家农场的地里,他说去参加婚礼,让我等他下午陪我去见杨老板,因为他们是老邻居,从小一起长大,关系好。我说等不及了,现在那两匹马还在人家杨老板的麦地里跑。三弟嘱咐我可以提他,杨会给个面子。我和三弟告别后,心不在焉的骑着摩托车往山上走,觉得时间过得很快。我实在不好意思去见人家,但又不能不去。在上大岭时,我遇见了骑着摩托下山的杨二老板,我问他:“你哥在山上吗?”
他说:“在山上等你呢!气得不行!”
我说:“实在是对不起!这放牛的也太不争气,我可怎么和你哥去说呀?”
杨二老板又生气地说:“你们那个放牛的好像有点傻?我刚才想揍他了!”
我问杨二老板:“他又怎么了?”
杨二老板对我说:“刚才我遇见他了,就在前面,手里还拿着一个半导体收音机,在听歌曲,我告诉他牛群又快要进地了,他看看我没什么反应,还是一心在听收音机,好像没他什么事?”
我为了缓冲杨二老板的情绪笑着对他说:“二老板不要生气,那个孩子确实是和正常孩子有所不同,我一会训他!”
匆忙地与二老板别过,一会就来到了农场。看到这时我那两匹进了人家地里玩耍的马已经被人家好不容易的抓到拴在那里,在冲着我打喷,我心想都是你们两个家伙惹得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