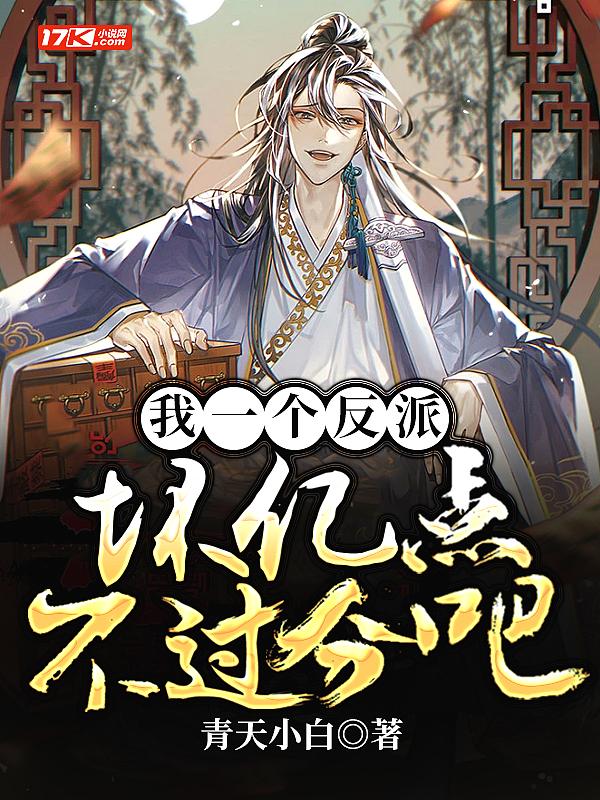69书吧>有瑕by > 第20页(第1页)
第20页(第1页)
齐弩良过去端了蜡烛,这十来平米的客厅,在昏暗的灯光里倒是十分宽敞。因为除了他腿边一张已经旧得掉皮的破沙,整个客厅空空如也,比家里遭了最穷凶极恶的小偷还干净。
除了蒋彧关上门的那间房,右边还有一间房,门虚开着。毕竟他目前只是个借宿的,便没有到处转悠,而是在这沙上和衣躺了。
齐弩良抱着胳膊琢磨,一个小孩,这两年他到底怎么过下来的。
看得出来,孩子过得挺苦。肉眼可见的瘦弱,比他这个蹲大牢的还瘦。
齐弩良也偏瘦,但他自信还有一身精瘦的肌肉,而蒋彧却像根直愣愣的竹竿。不过欣慰的是,孩子还算健康,跑得忒快,很是机警,想到这儿,齐弩良又忍不住苦笑。
他把手伸进衣服的内袋里,那里有个钱包,钱包里有一张女人的相片。齐弩良按住那个鼓囊囊的方块,像是按着自己的心,心里默念着让女人放心,他会好好照顾这孩子,直到他长大成人。
齐弩良蜷在破沙上,不知道什么时候睡着的。到了下半夜,他把自个抱得更紧,迷迷糊糊地觉得冷,好像四面八方都有凉风灌进来。明明他是睡在房子里的,却像是在旷野上一样,甚至还绵延不绝做着类似的梦。
接着他被一点暖黄的光惊醒,睁开眼睛便看见蒋彧缩手缩脚从他跟前经过,端着一根蜡烛。他也和齐弩良一样,穿着所有外衣,夹着腿,去了另一头的厕所。
厕所门推开那瞬间,齐弩良总算知道一直聚而不散的臭味儿是哪儿来的了。他听见了蒋彧尿尿的声音,却没有听见冲水。这家里不仅没电,还没水,难怪厕所这么臭。
蒋彧上完厕所又匆匆往房间走,这时,齐弩良才看见他没拿蜡烛的那只手,拿了一把起子。某个一晃而过的角度,起子金属头白闪闪的光直刺进齐弩良眼睛里。
“蒋彧。”
“啪”
!孩子吓得肩膀一抖,手里的起子应声而落,几圈滚到了沙脚下。这可吓坏了蒋彧,他忙不迭跑过来,想要捡起那把他唯一的“武器”
,却还是晚了一步。
齐弩良伸手捡起来:“你上厕所拿这玩意儿做什么?”
蒋彧不说话,但忍不住腿软,像一个被绑架者就要暗地里挣脱绳索时被绑匪现,像一个刺客还没露出真面目便败露,根据他以往的经验,这一切只会让他加找死。
齐弩良拎着起子朝他走过去,蒋彧想跑,可是他已经腿软得无法逃跑了。齐弩良把起子递给他:“拿着。”
蒋彧哪里还敢伸手接,即便拿着这玩意儿,在这样一个高大的成年男人面前,他也保护不了自己。
他紧张地反复吞咽唾沫,想要解释,想要说点什么让对方息怒。
“我……”
齐弩良把工具塞他手里,烦恼地抓了抓光头皮:“家里突然进了这么个陌生男人,你很害怕吧。不好意思啊,我没想到这个。”
“……”
“我先出去了,你安心回屋睡你的吧。”
说完齐弩良果真出去了,把门严丝合缝地拉上。蒋彧呆呆望着门口,他也很有些茫然。
坐在门外,齐弩良从烟盒里掏了根烟点上。他本身就是不擅长表达的人,也不爱说话。却没想到遇到个比他更不爱说的,要不是看他紧张兮兮地张了嘴,齐弩良甚至怀疑他就是个哑巴。
楼道里更冷,齐弩良把衣服拉链拉到顶,还是觉得漏风。就这么坐等天亮也不是办法,他站起来跺了跺步子,打算下楼去转转。
天快亮了,巷子里传来一些空旷的鸡鸣和犬吠,一些黑洞洞的窗户里亮起了灯。
晴朗的冬天早晨总有大雾,奶白色的雾气凭空泛起,渐渐充满这一条条脏乱差的小巷。
齐弩良缩着肩膀,毛线帽子上的绒线上结了白糖样的白霜,连他长眼睫上也都快结上了,只有叼在嘴边的红亮烟头一闪一闪,一些灰白色的烟混着雾气从他嘴里吐出来,融进了白雾里。
第一丝天光透出来时,梁麻子的早餐铺子拉开卷帘门,一屋子暖热的潮气和着食物蓬蓬勃勃的香气涌上街头,跟着一个煤炉子搬到门口,架上一口油锅,梁麻子当街炸起了油条油饼和油果子。
齐弩良鼻子耸了耸,抬腿进了店,成了店里第一个客人。
刚出锅的滚烫的豆浆,刚炸好的焦香的油条,和一盘咸菜,一起端到齐弩良面前。这会儿还没什么客人,老板坐他对面跟他搭讪。
“看你面生,不是咱这块的人吧?”
“不是。”
“走亲戚来的?”
齐弩良摇头:“我来找蒋彧。”
“找那小子,你是他什么人啊。”
“我是他舅。”
梁麻子皱起眉头,倒是知道这小流浪儿有个大姑,就在洪城城里,也不管他,从不知道他还有什么舅。
齐弩良知道自己以后就要在这片生活,就要和这些人打交道,也猜测这孩子大概受到过不少欺负,便多说了两句。
“我是姚慧兰表弟,她去世那会儿我没在家乡,也是最近才得到消息说孩子没人管,所以赶回来了。今后蒋彧就归我管了。”
今后,他就不再只是孤孤单单的流浪儿,任人欺负而没人和他撑腰了。
一提起姚慧兰,齐弩良心里便又多了不少酸涩和难过,忍不住打听她的情况:“姚慧兰……我姐,她有没有关系好的朋友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