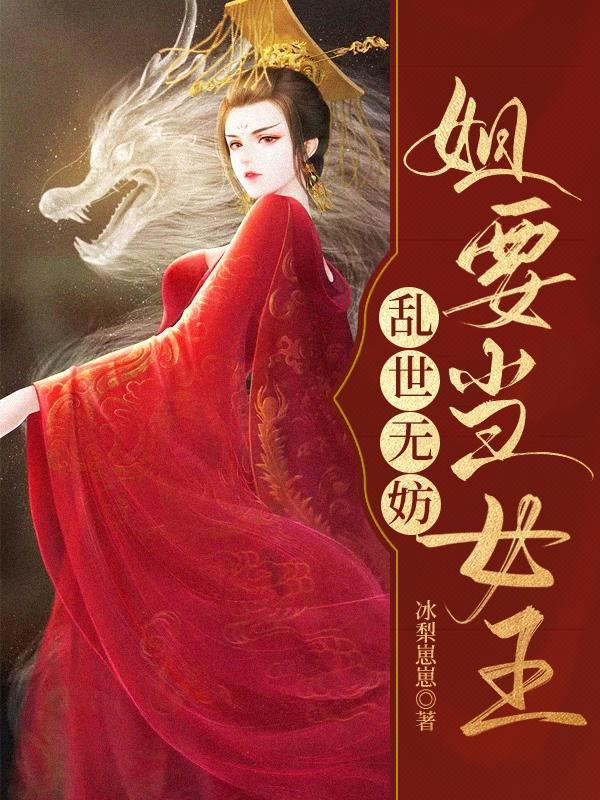69书吧>谁动了大佬的鱼摆摆免费阅读 > 第76章(第2页)
第76章(第2页)
“我记得佟佟小时候也这样,”
佟宇文说话有点€€结巴,“爸、爸那里不€€是€€一直备的有药膏吗,很管用。”
“早过期了吧。”
“应该没€€,爸清醒的时候交代过,隔段时间就更换,反正€€离得也近嘛。”
车辆不€€知不€€觉间换了方向,驶入另一侧道路。
到门口停下时,佟怀青一阵恍惚,还以为又看€€到了大片的紫色绣球花。
再定睛一看€€,没€€有,院子很久没€€人住了,虽说按时打扫,但毫无生机,哪儿还有花呢,只剩常青的松柏,静静地戍立。
去往二楼外€€公的书房,佟怀青拉开右手边的抽屉,正€€如他小舅所言,放了一管软膏。
是€€个外€€国牌子,很好用,小时候起湿疹了,抹上去没€€多久就能好。
外€€公就托人隔三差五寄回来,一直备着。
新的,没€€拆封,赵守榕他们在院子里说话,佟怀青拿起来看€€了会,把盖子拧开,闻到很熟悉的药味。
他抬手,摸着自己的脸。
湿的。
掉了眼泪。
心€€脏的钝痛姗姗来迟,痛到呼吸不€€畅。
连赵守榕都听见€€动静,冲进€€来推开门,佟怀青已经趴在凳子上,哭到浑身抖,连连抽气,喉咙嘶哑着喊外€€公,喊妈妈,腿软到站不€€起来,只有手紧紧地抓住那管药膏。
佟怀青大病一场。
高烧,烧得厉害,无论什么办法都降不€€下去,呕吐,连粥也喝不€€进€€,靠着点€€滴维持代谢,手背上扎了留置针,脸颊烧成酡红,嘴唇干裂起皮,没€€有血色。
脑子昏沉。
很多事想不€€起来了。
想要小兔子陪自己睡觉,想要用池野留给他的杯子喝水,奇怪,池野怎么还不€€回来呢。
说好了,要来接自己的。
不€€对。
佟怀青终于睁眼,看€€着吊瓶里的液体,恍惚觉得,会不€€会是€€池野不€€知道,要来哪里找自己呀。
那我一定要快快好起来。
佟怀青这样想着。
然后,我自己去找他。
他尝试着吃东西,缓慢地咀嚼,吐过就歇一会,喝完水再吃,那个廉价的玻璃杯一直放在床头柜,保温效果出乎意料,热水倒进€€去,到了晚上,摸起来还是€€温乎乎的。
赵守榕和佟宇文白天会过来看€€自己。
他俩似乎存在分歧,彼此之间的气氛不€€太€€对,小舅是€€个性格非常平和的人,圆脸蛋上总是€€有淳朴的笑意,但当他看€€见€€赵守榕时,却会气哼哼地背过脸去。
有次,佟怀青听到他们在外€€面争吵,赵守榕声音很大地说了句:“我是€€他的监护人!”
然后,小舅就生气地回了什么,说话结巴,只能听清房子和珠宝这两个词。
佟怀青累,谁都不€€想理€€。
扭头睡觉。
直到半夜被惊醒。
他睡觉实在太€€轻了,走廊外€€面的脚步声都能吵到他,佟怀青不€€知道医院那边怎么安排的,反正€€这几天,除了楼下偶尔车辆经过时的鸣笛,他什么声音都听不€€见€€。
所以那束手电筒的光扫过来,佟怀青立马睁开了眼睛。
斜斜地照在天花板上,像一枚小月亮。
与此同时,窗户被从外€€面推开,佟怀青做梦似的看€€过去,一个高大的身影正€€在推开窗户,黑衣黑裤,宽肩窄腰,攀着窗台的边沿,轻巧地一跃而下。
佟怀青的心€€剧烈地跳了起来。
池野收起手电筒,按灭了天花板上的月亮。
“你怎么才来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