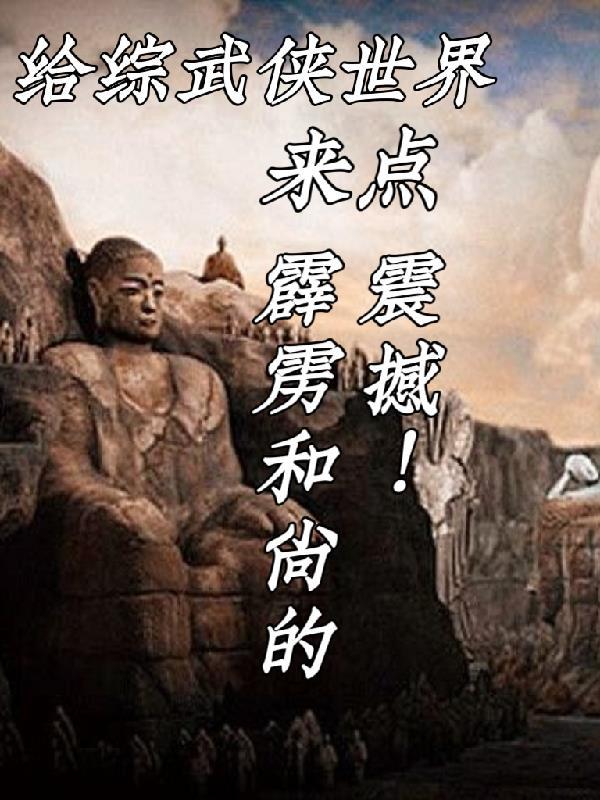69书吧>风起之时剧本杀角色 > 第75页(第1页)
第75页(第1页)
屋里没开灯,只有一堆电子仪器出蓝莹莹的光,仪器摆得密,又重叠摞起,除了有好几块清晰度不一的电子屏,其他全是大大小小的电线,线头连接处闪烁着各色光点。
电子仪器光亮有限,屋子的另一边全隐没于黑暗。
黑暗中亮起一道火光,紧接着,一点火星子迸开来,燃起猩红的光亮。烟气冉冉上升,模糊了被火光映亮的面孔——眼神如鹰般锐利,两道粗眉横在眼睛上方,脸上的纹路像是一刀刀割出来的,鼻头又很深厚,脸下颌全是胡茬。
“滑头告诉我,你今天刚回来。”
抽烟的男人低低嗯了一声,浑厚绵长,有些疲倦。
高冈摸到门后的开关,往下一按,电灯管滋了两声,房间终于亮堂起来。
这地儿十多平米大,墙角搁一张折叠床,床上被子老旧,长期不换洗,生生睡出一个人形。一根拐棍倚在床头,细伶伶的脚,金属制的,在电灯下通身亮。床头一张小桌子,摆满酒瓶,空的、满的、喝了一半的,歪七扭八倒在那儿。
酒瓶下压着各样的记,都是随手写的,有些被揉成团,随意扔在地上;不止酒瓶下有,墙上也有。贴在墙上的记,用红色重点标记过,多是对案件的梳理,或者是一些人物档案。
房间的主人深吸一口烟,走到桌旁,姿势有些奇怪,似乎是腿脚不大好。他扫荡干净桌上的杂物,又从地上扶起一只板凳,示意高冈坐下。
“你那案子有眉目了?”
那人又吸一口,把烟头摁灭了扔在烟灰缸里。
“考古队遇害一案,附近出现了绑走三个孩子的嫌疑人的踪迹。同样的,现场没有找到他的指纹。”
“难怪要来找我。”
他起身来到床边,拿起床头的那根拐杖,拄着拐,又回到高冈身侧。粗砺的手指抚上墙面,一张张挪动,最后停在靠近墙脚的位置——那里记是近贴上去的。他一把撕下,放到高冈面前。
纸上是男人龙飞凤舞的字迹,高冈勉强只能看懂一点:“你这字越写越潦草。”
“是怕被人认出来。”
“我查到一点东西,你可能会有兴。”
男人不再继续高冈的话题,坐到他对面,说:“就从李家村说起吧,帮助嫌疑人从那边逃走的,确实是大乌树的人。”
大乌树,对这个名字,高冈再熟悉不过。
当年就是这个地下组织,接下了暗杀他师父的单子。
“背后是谁在交易?”
男人摇头:“我没有查到,但可以确定的一点是,大乌树不单纯是一个杀手组织,在它背后,还有更深的势力。”
高冈心下拔凉:“你是想说,这不是简单的非法交易,没有雇主、没有佣金,一切行动都是大乌树自己,或者说是它背后那个势力的意思?”
男人点了点头:“这是目前最为合理的猜测。”
照这么说来,他们所了解的大乌树,难道只是冰山一角?那么冰面之下,又会是什么?
也难怪千里眼没查到线索,他这人虽然小气鸡贼,却也知道有些底线不能碰,比如说暗。网,打听这种信息,若是不懂得收手,迟早引火上身。所以干脆全绕道走,好落个干净。
见高冈不说话,男人补充:“还有一点,嫌疑人用的那辆车,也是大乌树提供的。你回去看,保不准能找到大乌树的标记。”
“留了标记?故意的?”
男人换了个姿势,靠在墙上,手按摩着右脚:“应该是。”
高冈瞥到男人的动作,皱起眉头,起身走到男人面前蹲下,强行掀他裤脚检查。检查完了,没什么问题,高冈悬着的一颗心这才落了地,他抬头责问男人:“你何必这么认真,脚废了你才开心是吧?”
男人笑了笑,没接话。
见他沉默,高冈放下男人的裤脚,站起来,托着腮帮在屋内打转:“不愿暴露行踪,却又让大乌树故意留下线索,看来是专门给警方看的。”
能耐确实大,居然敢让大乌树暴露自己的标记。
“时候不早了,你小子还不走?”
男人重点起一支烟,将神情掩在烟雾之下。
得,屁股还没坐热,又一次被下了逐客令,每回来都这样。
“你还没告诉我,大乌树标记长什么样。”
男人盯了高冈半晌,蓦然脸色一松,不耐烦骂了句:“烦人。”
他用牙齿叼着烟,手挽袖子,露出古铜色小臂。一手把台灯拉低,橙黄的灯光打在男人手臂上,靠近臂弯处有个纹身,是一只独木舟,舟上载满粉色的花瓣。
大乌树的标记,不是黑色的树,是一只船,满是花的船。
-
高冈正要走,忽然想起一件事,又折返回来:“为什么要让叶湑做特情?真想利用千里眼的力量,不用借助她,警方也搞得定。”
男人原本拿起空酒瓶准备掷过去的,听到叶湑的名字,瓶子在手心里转了一圈,又回到原点。酒瓶被放回到桌上,他认真地回:“我自有打算。”
“她也是受害者,什么都不知道,不该被牵涉进来。”
“你错了,”
男人摇头,“她已经被盯上了,只有一直在我们的视线里,才能保证她的安全。”
高冈大约猜到男人这话的意思,但他还是想听男人亲口说,好打破他之前不切实际的想法:“怎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