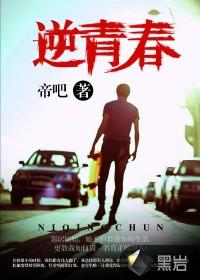69书吧>公主,我不想努力了(重生) > 第 78 章(第1页)
第 78 章(第1页)
馒馒……
玄乙已经许久没有听过这两个字了。
前世。
玄乙和陈天忌成婚的第二年盛夏,殿试放榜,问鼎状元的学子叫桑子梳,是陈天忌在落英书院时的同窗,也是珞城人。陈天忌受邀去桑子梳家里吃酒,最终喝了个酩酊大醉回来。
这位状元的事玄乙早就听说过,他家境贫寒,多亏陈天忌的父亲、当朝宰相陈文忠资助,才能同陈天忌一起在大衡数一数二的书院里读书。他倒也不负众望,寒窗苦读十数年,各路考试过关斩将,年纪轻轻便拿了状元。陈相也为他高兴,听说还收他做了义子。
陈天忌吃完了状元席,东倒西歪回到了公主府,下人们一口一个“驸马”
地伺候着,他都将他们一一推开,就连从小就伺候他的侍从若无,陈天忌也不让他碰一下。
婚后的玄乙已经尝够了陈天忌的冷脸色,两人又一直是分房睡的。玄乙知道他今日是去赴他同窗好友的宴会,估计会回来得很晚,所以也没等他,径直在自己的院子里躺下了。
谁知刚入梦乡没多久,就听见有人“哐哐”
敲她的房门。
她起身披了件蚕丝薄纱,想开门看看是谁这个时辰了还要扰她的清静。
结果门刚一打开,陈天忌就“扑通”
一声趴在了她脚下,将玄乙吓了一大跳。
玄乙顶着一身酒气,将陈天忌扶起来,陈天忌却赖在地上,
眯着一双醉眼,回头指着天上的月亮说道:“月亮!好大!好圆!好像你的脸啊李玄乙!”
玄乙的双手都架着陈天忌的咯吱窝将他半抬起来了,一听这话,气得差点把他又扔回到地上。
玄乙好不容易将他扶到茶几边上坐着,陈天忌屁股沾上椅子之后,人倒是乖巧,乖乖低着头,等玄乙给他倒水喝。
此时的玄乙虽然已经知道陈天忌不喜欢她,甚至讨厌她,但毕竟是从小就放在心上的人,陈天忌除了不对她笑,不怎么同她讲话,也没什么更让她生气的行为。故而两个人还没到相顾无言的时候。
玄乙将水杯递到陈天忌手上:“吃酒吃得高兴了?”
玄乙自幼认识陈天忌,各路宴会上,陈天忌何种形貌她都见过,喝醉了的陈天忌她还是头一回见,自然以为他这是酒逢知己千杯少。
陈天忌咕咚咕咚把水喝下去,又将杯子递给玄乙:“还要。”
玄乙无奈,接过杯子继续给他倒水。
就在这个空挡里,陈天忌突然滔滔不绝起来:“子梳这篇文章我看了,遣词造句还是太小心,怕得罪人,写得太浅。如今大衡的朝堂看着花团锦簇,其实内里头已经开始败了,党争、贪贿、徇私、枉法。如今这些官员在官场上浸淫多年,骨头早就被泡软了。就连我父亲这样的刚正之人,参奏之前都得先掂量掂量那人背后的人脉和势力,会不会牵一发动全身。如
若初入仕的学子们也都瞻前顾后、曲意逢迎,朝廷就会更加乌烟瘴气。若是我参加殿试……若是我……”
话说到这里,陈天忌的醉意似又翻了上来,舌头又打起了结,说话含混不清起来。
玄乙又将水杯递给他:“若你参加殿试,你会针砭时弊,慷慨直言吗?”
陈天忌接过水杯,像是着急证明什么似得,梗着脖子看着玄乙:“我会!我当然会!不过可惜……我再也不能参加殿试了……”
陈天忌说完这句话,似乎知道自己这样说有些不妥,低下头小口小口地啜着水。
玄乙这是第一次从陈天忌口中听到他的遗憾,她的心头也酸涩起来,如果不是他们俩的这桩婚事,今朝金榜题名的,是陈天忌也未可知。
“不过没事。”
陈天忌忽又将头抬起来:“我参加了也得不了状元,我爹不喜欢我,他就喜欢子梳那样的,会来事儿,八面玲珑的。我爹不喜欢我,我娘也不喜欢我,我是庶出,白白占了嫡出的便宜,我们家人都不怎么喜欢我。”
这倒让玄乙意外了,陈天忌打小就是珞城王公子弟的翘楚,文武双全,又生得好看,去到哪里都是众星捧月,除了是庶子抬的嫡出的身份,再没什么可以让人指摘之处。
可是……庶子怎么了?陈天忌作为庶子被抬上来,不正是因为相府没有嫡子,陈相和他正头夫人没有儿子,而他又偏偏想要个嫡子吗?你
们自己生不出来,反过来怪陈天忌?
“你很好。真的很好。”
玄乙自己也是庶出,对陈天忌的处境颇为感同身受。
“你有小名吗?”
陈天忌又转了话锋,笑着问:“我有小名,我的小名叫小剩儿,你猜猜是哪个剩?”
话虽这样问,但不等玄乙说什么,陈天忌就自己先说了答案:“剩下的剩。我娘……哦就是我姨娘,是乡下人,没读过书,也没什么见识,她跟我父亲青梅竹马,但她出身寒微,我父亲平步青云之后,她便只能做妾。她还是乡下那套习性,说天忌这个名字不好,老天爷都忌惮,太霸道,还是要取个贱名儿,要不然这辈子会过得很苦。所以我就叫了小剩儿。”
玄乙听了,不以为然:“虹、霓、彗星者,天之忌也。彩虹是你,流星也是你,多好的名字。”
陈天忌愣了愣,接着便因为笑意醉眼弯弯:“那你呢?你有小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