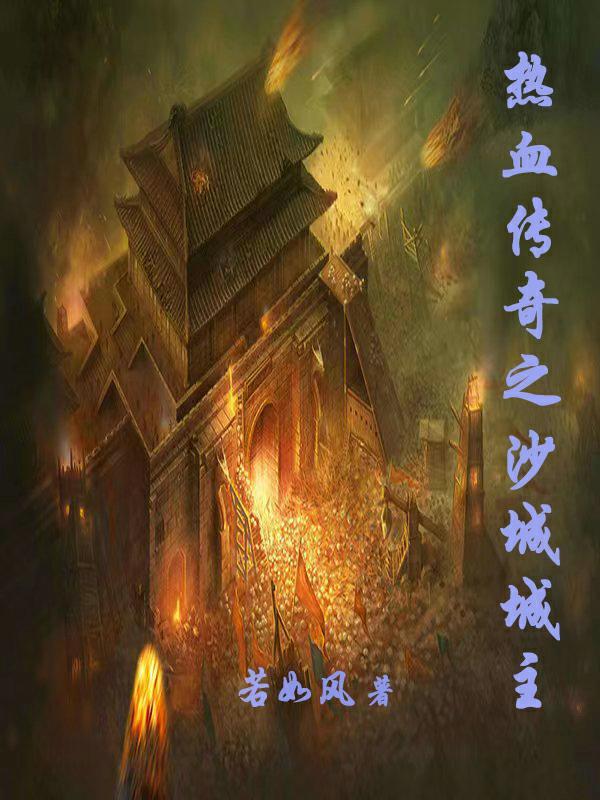69书吧>女尊摄政王的宠君免费阅读 > 第42章 这两年来孤还真没有愧过亦不曾悔过(第1页)
第42章 这两年来孤还真没有愧过亦不曾悔过(第1页)
钟离沁径直去了关押右相的牢房,那候在门口的人见了她,齐齐跪下便要大喊,她一抬手,阻止了他们的动作。
“不必宣扬。”
轻飘飘的丢下一句话语,钟离沁先一步走了进去,刚到了一处拐角,耳边便听到了里头传出来的,似有若无的谈话声。
好像是君后和右相,钟离沁放缓了脚步,慢慢的继续靠近,不多时,她便彻底听清了两人的谈话。
“我听宫人说了,阿沁一会儿就过来了,您放心,她好歹也是您的学生,只是想听您说一句软话罢了,不会关您太久的。”
应陶儿看着牢房里仅仅两日不见,变得十分憔悴的右相目露担忧,可一想到杜欣会变成这样的原因全是她自找的,又不由得怪了一句。
“您也真是的,为何要在朝堂上说这样的话呢?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将阿沁的脸面往哪搁?”
不要说钟离沁了,就算是他也是得生气的,要不是念在杜欣是三朝元老,在朝中又有极高的威望,怕是早就被就地正法。
“一会儿她来了,您可千万不要再说这些…”
“这些大逆不道的话?”
被打断了,应陶儿面色难看起来。
“老师,您知道就好。”
右相笑了笑,对着应陶儿缓缓摆了摆手,她是年纪大了,但还没有老糊涂,而她也相信自己看人的目光,如年轻时一样毒辣。
钟离沁就是天生坏种,这是改不了的,也是她一个先生教不会的,天命里讲的,果然非她此等凡人能够转变。
所以,右相仍是回道:
“老臣的话没有半句虚假,信不信,随君后殿下自己斟酌。”
“…”
应陶儿彻底没了话语,右相被关了两日,他也往这牢房里跑了两日,口水都说干了,还是没能劝动这顽固的老人家半分。
他十分心累,因为他不管怎么解释,右相都还是笃定当年杀害钟离眠的人,就是钟离沁。
他不想管了,既然右相不听劝,他又何必自讨没趣呢?他这般帮着右相,若是惹恼了钟离沁,对他一点好处都没有。
“老师,我幼时与钟离姐妹相识,有幸得您几日教导,所谓一日为师,终身为母,我敬您爱您,但您所说的,我不敢苟同。”
应陶儿叹了口气。
“我知道,不管我说什么,你都不会改变对阿沁的想法,我想我们还是勿要再谈了,一会儿阿沁来了,我不敢求您说句软话哄她开心,少说两句刺耳的便可,哪怕一声不吭也是好的,她能来看您,就证明她是想放您出去了。”
放她出去?摄政王还真是宅心仁厚,但是可惜她不吃这一套,右相耷拉的眼皮下,一双眸子丝毫不显浑浊。
“我知你怕她,也是,圣上年幼,你们父女必须依靠着她,君后殿下,你倒是真向着她,她若是要自己坐上龙椅,可是轻而易举的事。”
闻言,应陶儿不由气极。
“您说的对,我是怕她,可当年若是没有她,念音不可能会坐上那个位置,您也说了,只要她想,她完全可以成为北牧的国君,那她为什么不这么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