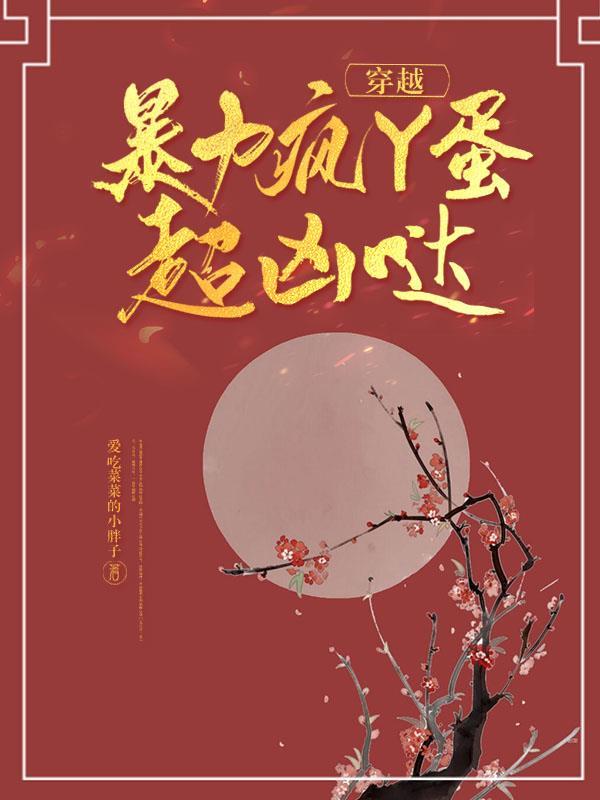69书吧>重生后太子妃咸鱼了128章 > 第70节(第2页)
第70节(第2页)
皇帝方才是一时兴起,回过头来一想,也觉不妥,便另赏了一把枫木螺钿琵琶并绢帛若干匹。
何婉蕙谢了赏,坐回末座。
皇帝对尉迟越笑道:“三郎方才来得巧,正好评点评点,阿耶这曲新谱的《怨歌行》如何?”
尉迟越面无表情,淡淡道:”
阿耶雅兴,儿子不通音律,不敢妄加评鉴,阿耶谱的曲自然是极高妙的。“
这回答自不能叫皇帝满意,他抿了抿唇,又看向儿媳:“太子妃想必雅善音律。”
沈宜秋福了福:“圣人谬赞,妾于此道一窍不通,着实惭愧。”
皇帝有些扫兴,这儿媳正当妙龄,却这般无趣,白白浪费了这好相貌。他看了一眼何九娘,越发觉得这般才情态度方可称尤物。
五皇子饮了口杏酪,放下碗,忽然道:“阿耶今日怎的有此雅兴?”
皇帝妙善音律,昔年极好乐舞,谱曲作歌编舞无所不精,但近年来只顾着求仙问道,倒是将这些凡俗的喜好撂下了。
皇帝看了一眼何九娘,捋须笑道:“方才在书斋中见到九娘所书《怨歌行》,忽然有感而发,便谱了此曲。”
贤妃道:“圣人一刻钟不到便谱成此曲,一气呵成,真真如有神助。”
皇帝叫宠妃恭维得通体舒泰:“那也是九娘的诗和得好。”
五皇子道:“表姊还作了诗?那我定要拜读拜读。”
何婉蕙头皮一麻,这魔星一开口,总没有好事,正想着如何婉拒,贤妃却道:“阿蕙,你表弟想看,便与他看看又如何。”
何婉蕙只得从卷轴架上取下方才那页曲谱,卷起呈给尉迟渊。
尉迟渊往前展开,发现这曲谱原是缀在何婉蕙的手迹后头,卷首是班婕妤的《怨歌行》,接着是何九娘拟的同题诗。
五皇子歪着脑袋轻声诵了一遍,也不说好,也不说不好,只一味地笑。
何婉蕙兀自忐忑不安,便听他道:“表姊此诗深得古意。”
何九娘松了一口气,总算这浑人还有几分清醒,在皇帝面前不敢大放厥词。
正思忖着,尉迟渊却又接着道:“昔有班门弄斧,今有班门弄歌,妙哉妙哉。”
沈宜秋忍不住弯了弯嘴角,简直有些怜惜何婉蕙,牙尖嘴利之人不在少数,敢当着皇帝、太子的面说这种话,普天之下也只有五皇子一人。
这话说得促狭,连尉迟越都不免牵动了一下嘴角。
皇帝也是又好气又好笑,瞥见何婉蕙眼中泪光闪闪,立即板下脸道:“五郎,不许作怪!快与你表姊赔不是。”
尉迟渊放下诗卷,向何婉蕙作个揖道:“是我口无遮拦,表姊切莫放在心上,表姊的诗自是极佳的,不然阿耶也不会以曲相和。”
何婉蕙听他语气诚恳,却依旧在含沙射影,不由将下唇咬得发白,皇帝碰巧看见她作的诗,又不是她有意叫他看的,他要以曲相和,莫非她还能拒绝?
她自然看得出皇帝的眼神中不止有长辈对小辈的关爱,更有男子对女子的欣赏,这眼神她并不陌生——她平生所见外男不多,但十个里有八个这么看她,只因她生得美貌,又富有才情,难道也能怪她?
她心属的是太子,对皇帝并无什么想头,心中光风霁月,一派坦荡,但贤妃心胸狭隘,素有醋癖,听了这话保不齐生出什么误会来。
她觑了觑姨母脸色,果见她面露不豫。
何婉蕙心中恼怒,却不能对皇子甩脸子,只得道:“五殿下喜欢说笑,能博殿下一笑,是九娘之幸。”
皇帝打了几句圆场,将此事揭过不提,贤妃看了眼更漏,命宫人摆膳。
几人仍旧围着前日那张大方几案用膳。
酒过三巡,皇帝放下酒杯,对着下面挥挥手,舞茵上翩翩起舞的教坊女子便即行礼退下。
皇帝对身边黄门点点头,那黄门退出殿中,不一会儿,领了十来个女子,都作女冠打扮,身着青绢罗道服,头戴银莲花冠,个个婀娜俏丽,柔媚生姿。
![女道君[古穿今]](/img/149516.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