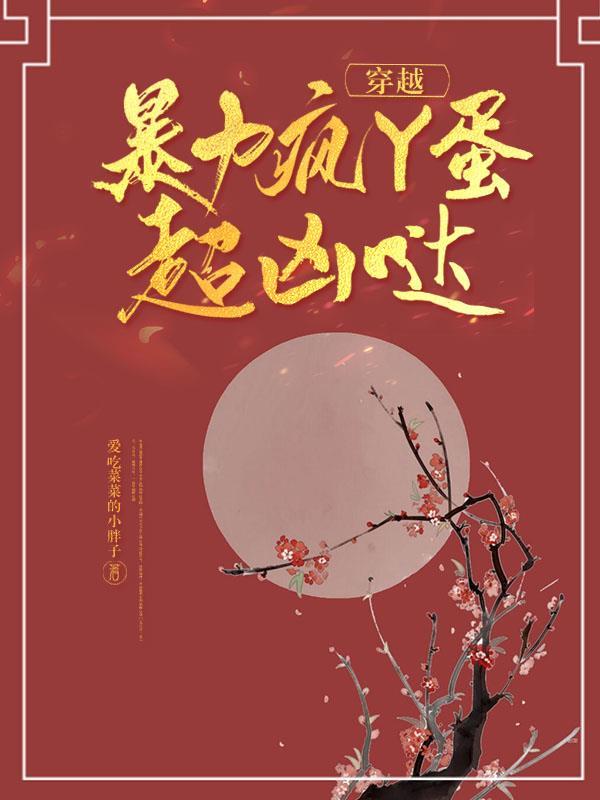69书吧>重生后太子妃咸鱼了128章 > 第70节(第3页)
第70节(第3页)
皇帝对这些女子道:“还不拜见太子与太子妃。”
众女子齐齐向尉迟越下拜,娇声道:“奴婢见过太子殿下,太子妃娘娘。”
尉迟越叫他们叫得起了层鸡皮疙瘩。
一见这阵仗,在场众人都知道是什么意思。
尉迟越不觉去看沈宜秋,却见她一脸无动于衷,端着茶杯的手稳稳当当,连罗绣都不曾颤一下,不由胸中发堵。
皇帝果然道:“往后你们就是东宫的人,须勤谨伺候太子、太子妃。”
众女齐声应是。
尉迟越却道:“多谢阿耶美意,但儿臣宫中不缺侍奉之人,儿臣正欲趁年下放归百名宫人。”
皇帝知道儿子是揣着明白装糊涂,但儿子的房里事,他这做父亲的实在不好插手,便看向贤妃。
贤妃会意,笑道:“傻孩子,放归宫人是福德,你只管放,这些人又不是与你做杂役的。”
她顿了顿道:“你后院中只得三人,成婚至今,也无佳信,便是做耶娘的不急,朝臣也要急了。”
说罢瞟了一眼儿媳,脸上露出得意之色:“不止是为你,也是为阿沈分忧。”
提到皇嗣,皇帝也皱了皱眉,脸色凝重起来:“你也不小了,诞育皇嗣刻不容缓,再无佳信,如何向百官与万民交代?”
贤妃见皇帝替她撑腰,霎时忘了对儿子的畏惧:“听听,阿娘是后宫妇人,不识大体,我的话你不听便罢了,你阿耶也这么说,你总要放在心上。”
两人这话是对尉迟越说的,却都看向沈宜秋,谴责之意溢于言表。
沈宜秋心知自己得表个态,请个罪,再拜谢皇帝的好意,将替她“分忧”
的美人收下来,回去劝谏太子广播雨露——这便是太子妃的职责所在。
她正要履行太子妃的义务,却听尉迟越道:“启禀父皇,此事乃是三郎之过,是儿子力微才薄,不堪大任,只能以勤补拙,埋首案牍,以至于无暇他顾,与太子妃无涉。”
沈宜秋微微一怔。
尉迟越伸出手,隔着袖子握了握她的手,一股暖意透过织物传到她手上:“是三郎无暇去后院,三人与三十人、三百人无异,且要安置这些人,又须营建、修葺宫苑,不免靡费,实在无谓。”
皇帝脸色微沉,但他执意不要,他强行塞人总是不像话,只得作罢,皱着眉道:“为政之道,在垂拱而治,不必事事亲力亲为,要懂得轻重缓急。”
尉迟越心中苦笑,国计民生,边情外政,哪一件是可以放手的“小事”
了?不过他还是拜道:“谨遵阿耶教诲。”
沈宜秋听皇帝大言不惭地教导尉迟越“治国之道”
,不禁哑然失笑,若不是因他十几年的“垂拱而治”
,太子何至于累成这样?
撇开上辈子他们之间的是非恩怨不提,尉迟越为君却是无可指摘,他御极数年,减少税负,藏富于民,便是有内忧外患,百姓也可称安居乐业。
他夙兴夜寐,还要时不时为皇帝的无理要求奔走,如今还要受此非难,实在荒谬至极。
沈宜秋胸中生出股意气,政不觉从袖管中伸出手,用力回握了太子一下。
text-align:center;"
>
read_xia();
![女道君[古穿今]](/img/149516.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