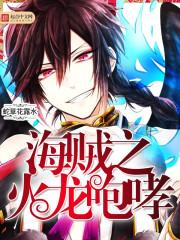69书吧>三国群英传大宋江山 > 第十二回(第3页)
第十二回(第3页)
苏逢吉义正辞严道:“我一心为国,从来就没有与你们争权夺势。你们既然不许郭侍中出任天雄军节度使,那么就推举一人罢。”
高行周年老体迈,符彦卿又要镇守青州,除了郭威,再也没有别的人选了。史弘肇和杨邠面面相觑,答不出话来。苏逢吉心中冷笑,逼问道:“史太尉执掌禁军,杨枢统领枢密院,难道找不出一个合适的人选吗?”
史弘肇心中暗骂苏逢吉老奸巨猾,道:“要郭侍中出任藩镇不是不行,不过要保留枢密副使的职位不变。”
苏逢吉瞪大眼睛,神情惊讶,仿佛听到最不可思议的话,道:“自古以来,就没有地方官兼任枢密使的道理,史太尉觉得这样行的通吗?”
史弘肇据理力争,道:“一则郭侍中乃是国家重臣,朝廷不能亏待。二则北军骄横,难以驯服。只有枢密副使的职位不变,方能镇的住那些骄兵悍将。”
杨邠道:“既然朝廷信任郭侍中,就应当把河北的防务都一并交给他。到任之后,节制河北诸州军马,居中指挥,方能更好的抵御辽军。”
史弘肇道:“对极,还要节制河北诸州军马,不然各自为战,给辽国钻了空子,反而与国不利。”
苏逢吉见他们狮子大开口,断然拒绝,道:“岂有此理,你们这般说法,简直成了朝廷听任地方摆布,本相拒绝。”
史弘肇早就打定主意,道:“朝廷若不答允,郭侍中就不会赴任。”
苏逢吉道:“本相不信,除了郭侍中,没有人能够接替邺王。”
言罢出了大殿。
他们君臣争执的时候,郭威一直缄默不语。史弘肇道:“你为甚么一直不说话?”
郭威道:“我乃国家之臣,不论国家把我调往何地,我都毫无怨言。就算是要我做个州官,我也无怨无悔。”
这句话说的语气平静,似乎理所当然。杨邠道:“你心灰意冷了?”
郭威微微一笑,道:“我披荆斩棘,从区区一个小兵到了现在,真是跋山涉水,历经磨难,眼前这点小事算的了甚么?”
史弘肇咬牙切齿道:“这件事一定是苏逢吉捣的鬼,他处心积虑,无时不刻不想暗算咱们,只怕早就布下了这个圈套。”
杨邠嗟叹一声,道:“朝廷无人可用,真要郭侍中前往邺都赴任,只怕无法拒绝。”
史弘肇道:“眼下朝廷用人之际,决计不能退缩,否则就满盘皆输了。”
杨邠道:“是啊,郭侍中,陛下若是找你单独谈话,你决计不能答应。”
顿了一顿,又道:“倘若真的能保留枢密副使职位不变,再加上节制河北军马,就算大获全胜了。”
苏逢吉出了广政殿没有多久,就看见李业快步而来,当下停下脚步,道:“陛下不在广政殿,给史弘肇和杨邠气走了。”
李业道:“我知道,陛下在御花园,要我传你过去。”
苏逢吉点了点头,道:“走罢。”
两人并肩而行,李业道:“听说史弘肇和杨邠顶撞陛下了?”
苏逢吉点了点头,道:“他们一个执掌禁军一个统领枢密院,大权在握,左右国政,谁也没有放在眼里。”
李业闻得此言,顿时火冒三丈,道:“这两个家伙朋比为奸,不但架空了你,还架空了陛下,简直目中无人。”
言罢大牢骚。苏逢吉看准时机,有一句没一句的火上浇油。
来到御花园,只见刘承祐站在凉亭之中,苏逢吉走进凉亭,道:“陛下传臣,有何吩咐?”
刘承祐问道:“你们议的怎么样了?”
苏逢吉道:“郭威一直沉默不语,倒是史弘肇和杨邠上蹿下跳,他们说要郭威赴任也不是不行,但是枢密副使的职位不变,不仅如此,河北诸州军马都要受其节制。”
刘承祐脸色一沉,道:“他们果真是这样说的?”
苏逢吉颔道:“一字不差。”
李业吓了一跳,叫道:“藩镇兼任枢密使,还要节制河北军马,那不是成了名副其实的河北王吗?陛下万万不能答应。”
刘承祐问道:“相公答应没有?”
苏逢吉摇头道:“如此无理的要求,臣已经断然拒绝了。”
刘承祐斩钉截铁道:“换别的人,朕就不信,除了郭威,就没有人担此重任了。”
李业开玩笑道:“陛下,臣毛遂自荐,愿为陛下排忧解难,去做天雄军节度使。”
刘承祐白了一眼,讥道:“你以为行军打仗是儿戏吗?就你那两板斧,除了吃喝玩乐,再也没有别的建树了。”
李业不服,道:“陛下小瞧臣了,臣一旦认真起来,决计不输郭威。”
苏逢吉道:“陛下,眼下除了天雄军这一头,还有科考大典。自古英明神武的帝王流传千古,皆因文治昌盛武功盖世。平定河中、凤翔、长安叛乱,乃是武功。科考大典则是文治,两者应等而视之。”
刘承祐点了点头,道:“国家打了胜仗,科考大典也要办得热热闹闹,你用心去办,不要出了纰漏。”
苏逢吉应声说是,笑道:“前者平定叛乱,后者举行科考大典,在民间看来,这正是双喜临门。两件喜事接踵而至,真是天降祥瑞,预示大汉朝蒸蒸日上。”
李业笑道:“何止两件喜事,过不多久就是陛下寿诞嘉庆节了,这叫三喜临门。”
高行周父子来到福宁宫觐见李太后,两人走进宫中,只见李太后坐在椅上,当即拜倒在地。高行周道:“臣见过太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