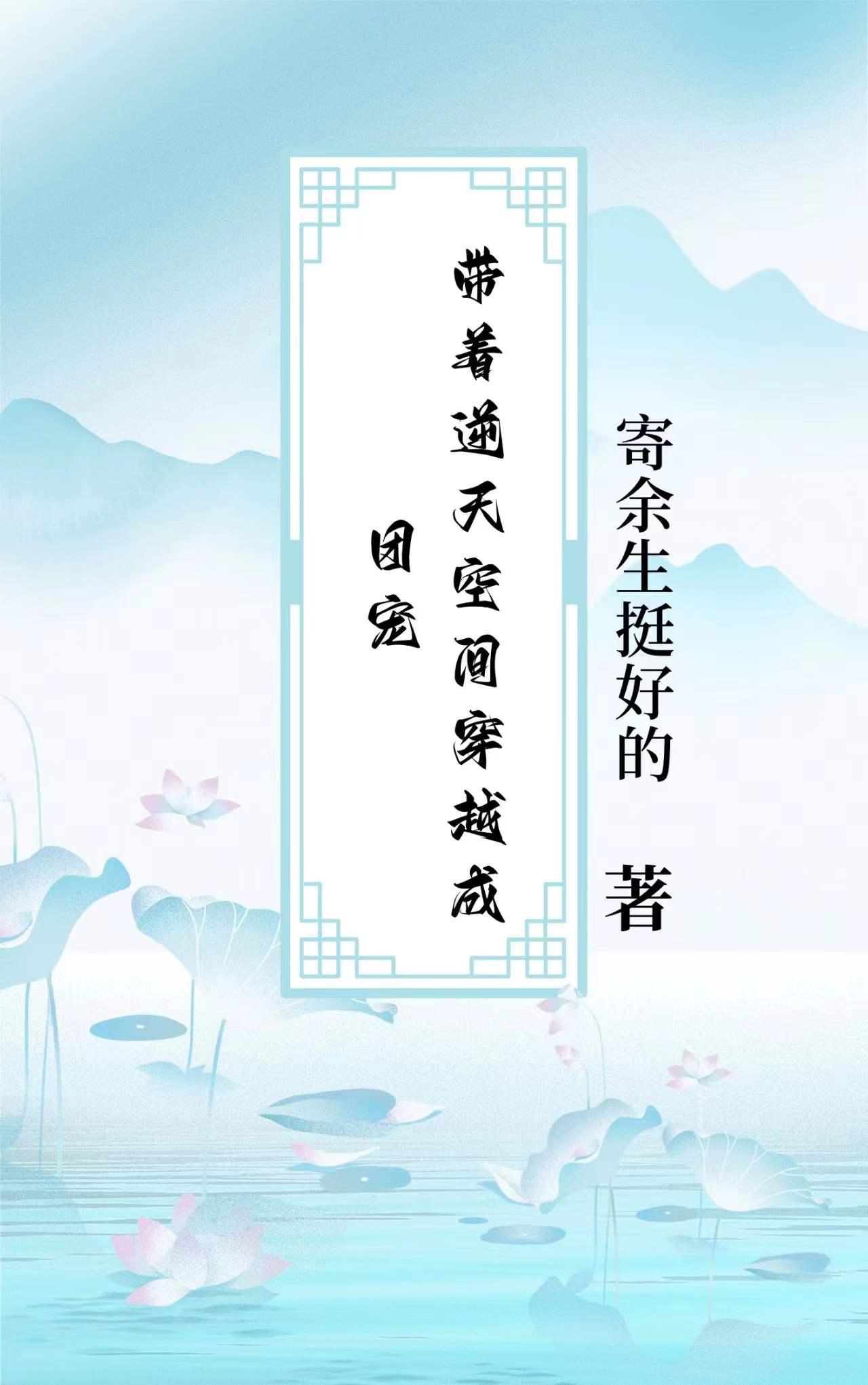69书吧>锦衣郎为什么指唐明皇 > 第三十五章英雄救美(第2页)
第三十五章英雄救美(第2页)
沈寒溪也不知自己是为何心烦,只觉得她面对自己时,全不像面对夏小秋那般放得开。他高高在上惯了,自然认识不到是自己的表达方式有问题。
他既不开心,那么错自然在她。
二人各怀心思,突然有个孩子撞了过来,与宋然撞了个满怀,一屁股跌坐在了地上。手中的糖葫芦,也滚落到泥泞中。
她被他这么一撞,衣服也被糖葫芦的糖衣给弄脏了,她却全不在意,蹲下来将那孩子扶起,为他掸了掸衣上的灰,问他摔得疼不疼。
那孩子却只关心地上的糖葫芦,作势就要哭。宋然忙牵起他的手,柔声安慰:“莫哭,我再去给你买一根,你看,那卖糖葫芦的还没走远呢。”
说罢像是终于寻到机会一般,对沈寒溪道,“大人,民女就先告辞了,今日之事,又欠了大人一个人情,待日后有机会,民女一定报答大人。”
她说着,微微施了一礼,便牵着少年到街对面追卖糖葫芦的去了。
报答他?她拿什么报答?
沈寒溪望着她行到街对面,买了糖葫芦塞到少年的手上,那少年拿着糖葫芦开心地跑开,她目送着他的背影远去,才总算想了起来,拿手轻轻掸了掸自己的衣服。
他立在人来人往的嘈杂和街市扰攘的喧闹中,突然想起许多年前。
他五六岁时,衣不蔽体,饥肠辘辘,好不容易在放粥的地方抢到了小半块馒头,从饥民堆里挤出来,跑得却略有些急了,不小心撞上一个衣着华丽的妇人。
那妇人见他弄脏了自己的衣衫,气得一脚将他踹倒在地,他却顾不上疼,伸手去捞那半块馒头。却眼睁睁地看着一只脚,重重地踩了上去。踩完之后,又在他身上补了好几脚。
那张扭曲到丑陋的脸,和她口中吐出的恶言,他至今都还记得。
如果说这么些年,是什么支撑着他走到今天,大概就是对那张丑陋的脸的厌恶吧。
没有更冠冕堂皇的理由,他只是讨厌人罢了,无比的。
他的思绪突然被人打断:“大人,贺兰大人请您回衙门,有事相商。”
他收回目光,对无声出现在他身后的影卫道:“知道了。”
又示意了一下宋然所在的方向,漫不经心地吩咐他,“去跟着前方那丫头,待她安全回到家,回来向我复命。”
“是。”
他又道:“记得前阵子,淳亲王想为王府的二公子在翰林院讨个职位,你去王府传本官一句话,就说凭二公子这副德性,若是当真进了翰林院为官,他这个当爹的少不得给他擦屁股,还是放过他自己吧。”
宋然回到家中时,钟伯和哑巴正在咣咣当当地修着屋顶,这屋顶年久失修,垫在砖瓦下的木材老旧腐朽,一下雨,水就顺着砖瓦缝哗啦啦往下掉。哑巴不在时,她心疼请小工的银子,一直没舍得修,现在有了免费的劳力,不用白不用。
钟伯在底下刨板子,听到她的脚步声,停下手中的动作:“少主回来了。”
宋然去厨房泡了一壶茶,拿到外面招呼干活的两个人:“钟伯,哑巴,先歇歇,明日再接着修吧。”
哑巴将眼前的板子钉好,顺着梯子爬下来,接过钟伯递来的一块手巾,道:“再有半日便差不多了。”
钟伯问宋然:“少主今日出去,没生什么事吧?”
她不想让钟伯跟着一起糟心,于是将那世子爷和沈寒溪的事隐去不表,只抱怨道:“票面上是一百两,却只兑了五十两银子,缩水缩得也太厉害。”
钟伯拿如今百姓时常挂在嘴边的那句话应道:“世道不好。再过几年,怕是连这五十两也兑不出来了。”
宋然感慨:“还是这沉甸甸的银子揣在怀里比较踏实。”
又望向微跛着脚走到水缸处洗脸的哑巴,“你的伤如何了?钟伯虽然通些药理,但到底不是专业的大夫,要不要再找个大夫给你正正骨,省得日后落下病根,连媳妇儿都娶不到。”
他往脸盆中舀着水,拒绝了她的好意:“不必,我也没有娶妻的打算。”
宋然望着他:“哑巴,你老实告诉我,你是不是为了躲夏小秋,所以故意装残?”
他默默地走到一旁,将那些废木料搬到墙角堆好,不回答她的问题。
宋然望着他来来回回的身影,小声问钟伯:“我是不是说中了?”
钟伯笑道:“他一身是伤,哪能那么快好了,少主这次应该是多虑了。”
宋然撇了撇嘴,道:“好吧。”
话音刚落,就听到有人敲门,她眉头动了动,前去开门。
一开门她就愣了,面前的人身材高大,虽是一身常服,但掩盖不了那孔武的体格和矜贵之气。
她惊讶道:“王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