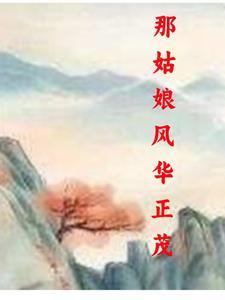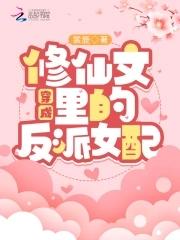69书吧>我来见你 > 第46章 新官(第2页)
第46章 新官(第2页)
温谨言看了他半晌,兀自释然似的一笑,没头没尾地道“没什么,陛下多次逢凶化吉,想必是个命带吉星之人。”
宇文曜愣了愣,一时没弄明白他这话什么意思,直到看到温谨言满脸得逞的坏笑着转过身去,才咂摸出味儿来。
敢情他刚才是想问自己有没有“乌鸦嘴”
体质?
可人已经走了,他这会儿再追上去理论就实在显得幼稚了。
从来占惯了嘴上便宜的宇文陛下在气人方面技高一筹的温大丞相面前败下阵来,切实体验了一把“天理昭昭报应不爽”
。
原本计划隔天一早出,奈何闵梁堆尸如山远比他们想象的还要严重,得亏西北现在的气候尚且凉爽干燥,否则只怕灾情未平,疫情又起。
于是为了妥善处理那些尸,一行人到底是多耽误了几天,期间宇文曜了一封手谕回暨阳,命令彭少阳就此事审问那些落网的山匪一番。
直到第五天午时过后,他们方才一切落定,重新整顿出,夜色将临之时顺利踏入了昆麓县。
昆麓县是距离昆仑山最近的一个县,受雪灾寒潮的影响最甚,可这里只有外患没有内忧,灾情下的百姓虽然形容枯瘦憔悴,神色间却依然带了几分生机,让人看了不禁颇为惊奇。
昆麓县的县令带着人前来的迎接,简化了规程却依然做得十分得体,连向来觉得这些礼节制度繁琐迂腐的宇文曜都不知不觉间顺其自然地承下了礼。
昆麓县的县令付理是个年轻有为的新任县令,布衣出身的年轻县令身上有着未被官场污浊压垮的特有朝气,他差人接手安置赈灾钱粮之后,便自请带着两位钦差大人视察灾情,一路上侃侃而谈,对灾情治理、后续的百姓安定、农耕之后如何复兴都有着一五一十条理分明的规程。
就连平日里惯于词严令色严加苛求的温谨言听着听着都忍不住流露出赞赏之意来。
谁入仕之初不是抱着满腔为国为民的热忱而来的?
可这浊世污泥横流,稍不留神便会沾染一身,或随波逐流,或泯然无踪。。。。。。
宇文曜看着付理眉飞色舞的模样,想起之前早早便萌生出来,却因后来意识到时局未定时机不足而被压下的想法来。
大耀的朝堂之中如今之所以颓然之势日盛,主要便是这年轻王朝内养了太多倚老卖老居功自傲的朝臣,其中不乏随着太祖开国的“要臣”
,他们矜功自伐,自以为仗着那些白纸黑字都已经开始泛黄褪色的书页上寥寥几笔记载的功劳便能一劳永逸安享到老。
他们大概从不明白,朝廷养他们,是出于仁义,并不是非他们不可。
宇文曜思及此,眼底闪过一丝带着讽刺的精光,那付理转头时刚好撞见,登时舌头打了个结。
温谨言早看到宇文曜走了神,心思压根不在这小县令身上,想着他昨夜没休息好,清晨又早早便醒了,又考虑到付理说的东西虽然可取,却到底不过是一个中规中矩的流程,并不是什么新奇的主意,听不听差别不大,便放任随他去,便没出声提醒。
只是没想到这一个不留神倒是把人给误伤了。
温谨言见状自认难辞其咎,便破天荒地出声替他解围“本官记得奏报上提到各地灾民暴乱的汇总,昆麓县也在其中,可怎么这一路走来倒是未见有暴乱的迹象?付县令方才也未提及此事。”
付理看了眼眼前的这位温丞相,又看了看方才眼神凌厉的“尚书大人”
,一时有些错乱,只觉得这道听途说的朝堂评论果然不可信。
只听说朝堂上有位面若冠玉心如蛇蝎的年轻温姓丞相,行事毒辣,居高自傲,从来摆的一副生人勿进的面孔。
可怎么从来没听说过还有一位一个眼神便如此吓人的尚书大人啊?
宇文曜已经回过神来,见那付理还在支吾,眼神都不敢往自己这边来,脸上不经意泄露出来的杀意收放自如,眨眼间便换上了惯用的忽悠伎俩,一派亲和无害的面孔“付大人?”
付理意识到自己失礼,歉然一笑“说来惭愧,下官不过是个百无一用的书生,手无缚鸡之力,让下官拿拿笔杆子写些规程倒还能献丑几分,当真要上马治暴民,那便是有这个心也没这份力了,这事儿还得感谢西北都尉大人。”
温谨言想到当时扫过一眼的名字,挑眉“哦?你是说张易谦张都尉吗?”
付理点头,翘着头朝前方不知道看什么“张大人前几日刚到此地,整治了暴乱之后听说钦差大人这几日便会途经此处,便说要留下面见请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