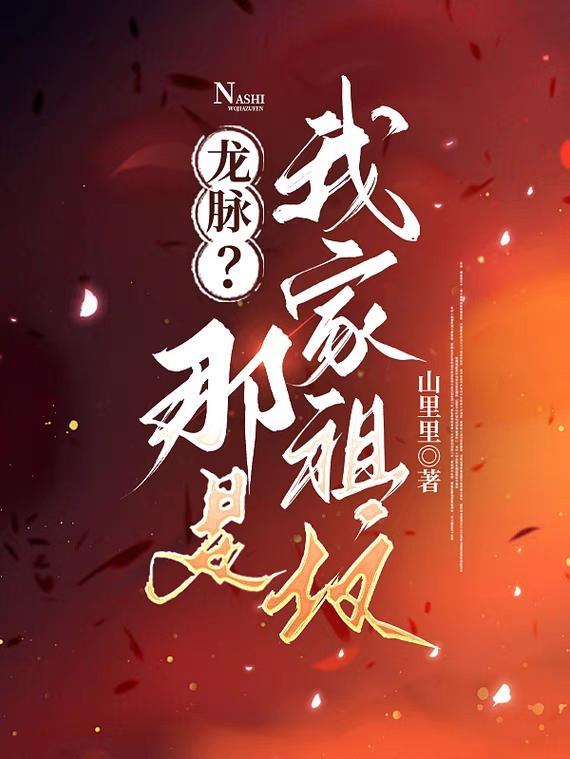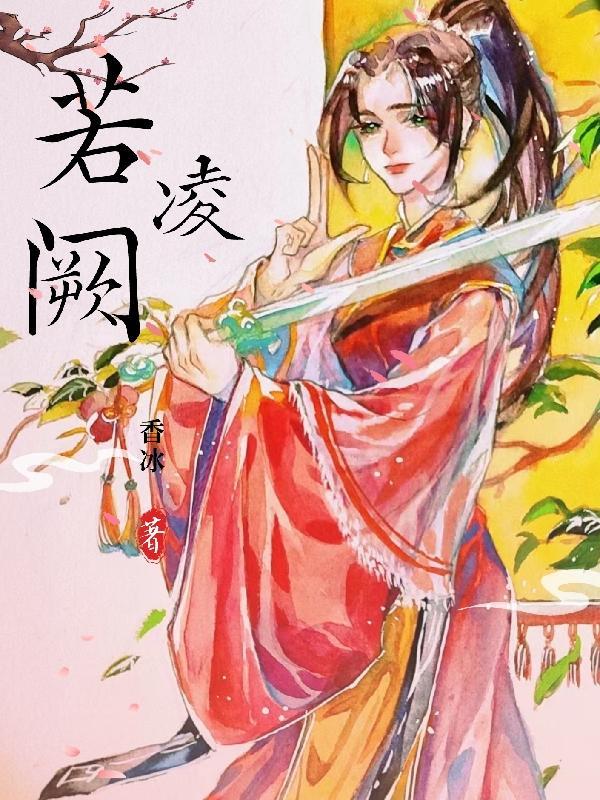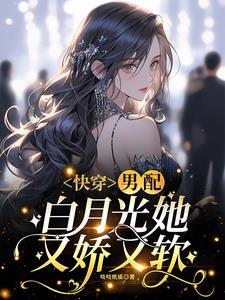69书吧>炊金馔玉不足贵免费阅读 > 第87节(第3页)
第87节(第3页)
只看那伙计背后的字,还是冤家。
便是当日狭路相逢没挣得了便宜的申大郎食店。
便是再傻,池小秋也知道,这宋太太是百般不愿让她接了这婚事的席面。
不愿便不愿,为何先前应了后头又去找别家去,倒费了她这几番功夫。
一番忙乱,堪堪只赚回了几张花笺的钱。池小秋托着脸在葡萄藤下生闷气,瞧着眼前的石墩子都想踢。
近日众人都忙。
往日道试最迟不过六月,今年提学官却久久未曾案临府城,直到了最近,府城里才递了信儿来,定了柳安长顺几镇考试的时间。
算是临门最后一箭,钟应忱也开始闭门不出温习书卷。
薛师傅整天占着院里头的厨房,不知捣鼓些什么新菜色,韩玉娘攒了许久的钱,终于挑了两匹好料子,这会终于逮住了池小秋,便忙过来。
“伸手,我量量这袖子得给你放多长。”
池小秋不情愿站起来,终于忍不住,将这事絮絮叨叨跟韩玉娘说了一遍。
“二姨你看,这不是耍弄人么!”
池小秋愤愤,她给人备菜一向尽心尽力,输给了有嫌隙的申家不说,还不知道到底差在哪一处。
“这有什么好奇怪的,不过是哪家太太拿捏未过门儿媳妇,找了你出气。你有万般好,只一样,是那彤姑娘喜欢的,她便不喜欢了。”
池小秋跟着韩玉娘转了个身,不由惊道:“都是一家人,为什么要拿捏来去的?”
“难道没听过那个曲儿?‘公婆堂上催做饭,小姑就叫裁衣裳,剪子未拿起,又要吃茶汤’(1),做娘的贴心贴肉好容易养大了儿子,娶了媳妇进来眼里心里有了旁人,哪个为娘的不难受?”
池小秋想不明白:“那为何还要应?”
“若是不应,岂不寒了儿子的心?”
韩玉娘失笑:“既是那小爷求的,怕是宋太太更窝着些火,听说还是个寡母,就更添了一层。”
她见池小秋失神,便宽慰她道:“总是占着理儿,便为难也不过一时的,谁都得走这一遭,多大的事儿。”
池小秋却不期然想到曲湖边的灯戏,钟应忱的话语响起来,同她的合在一起,下意识驳道:“那这儿子便忒不是个东西!坐看高堂为难新妇,是无情无能!”
韩玉娘吓了一跳:“说什么呢!这可是不敬!”
池小秋偏不听,扭了身子躲过去,坐在榻上触着凉意,支摘窗推出去声音有些刺耳,欲雨的天渐渐洇开成灰中还显白的不讨喜的颜色,暗沉沉的。
只有那熟悉的身形隔着河,隔着窗,每听到声音,便抬起来头,向她一笑,莫名心安。
她越长大,越见过更多的人与事,便知晓这许多与她认知相悖的道理,在旁人眼里通通都是,忍忍就好。
韩玉娘过得苦,可她是邻里眼里的“好妇人”
,她好像自在,可总是“不合时宜”
。
唯一能多些安定的,就是每每在“不合时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