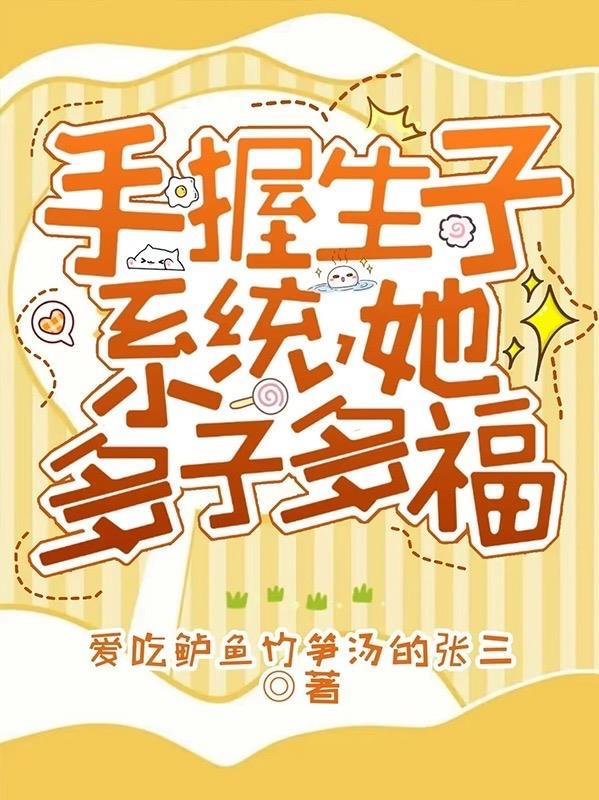69书吧>卧马沟的冬天吴根才结局 > 第十五章02(第2页)
第十五章02(第2页)
虎堆想拽着巧红赶紧回去,也照着月儿的样子准备准备,不然就真的没时间了。
看着虎堆拉拽着巧红下炕要走,耀先才犹犹豫豫吞吞吐吐地说:“虎堆,还有一件事要和你商量。”
虎堆下了炕都转过身要走了,听耀先说还有事,就停下脚等他说事。耀先再看看月儿,有些底气不足地说:“这也是月儿的意思。咱俩明天走了,她想让巧红上来搁伙做伴,吃住在崖口上,两个人在一起,咱们出门在外也放心,场院你也看见了,我围上枣刺咧。”
耀先的话也正说到虎堆的心窝上。男人普遍都有这样的心理,尤其是家里娶下模样儿好看媳妇的男人更是这样。男人出门上路,心里牵牵挂挂最放心不下的就是留在家里的女人。巧红雪蛋儿一样年轻漂亮,虎堆当然放不下心,可是他又想不出别的办法。耀先想出来的这个办法就可了他的心思,让巧红搬住到崖口上和月儿做伴他就放下心了。月儿多好呀,人样美,心也美。巧红跟上月儿只有好处没有坏处。“行呀,我也正为这事犯心思哩。”
虎堆很畅快地答应下来。
巧红实际上是空心箩卜,绣花枕头。表面上看雪蛋儿一样挺水灵,肚子里却啥都没有,有时候她连好坏都分辩不出来。不过她倒是很愿意上来和月儿做伴的。起码每天热热闹闹的有人陪着说话。巧红也干脆地说:“行,我就和月儿姐住一堆吃一堆,你们啥时候回来,我们啥时候散伙。”
四个人都朗声地笑了。
耀先虎堆走的当天巧红就真的搬上崖口和月儿住在一起,吃在一起,一家姐妹似的。白天干活,晚上睡觉,两个女人带着新生,挺自在的。只有一样事让月儿受不了,就是晚上躺进被窝哄新生睡着后,巧红唠叨出的一些话让月儿受不了。憨憨的巧红睡下后尽说些男女之间的事情,说得形象逼真露骨俗气,月儿就受不了。
月儿虽比巧红年长几岁,也比巧红早结婚几年,可是月儿并没有巧红这么多的经历和感受。月儿只是在婚后的第三天晚上才有过一次那样的经历,那种电流水漫的感受还没有涌遍全身,就被粗暴无情地打断。在后来这么漫长的日子里,他们虽然夜夜也在一起拥抱、亲吻、抚摸。但始终不能,顶多是在抚摸中用手指做一次替代。事实上月儿还没有真正享受过那种如仙如醉的生活,她和处女没有太大的区别。谁能知道美丽善良的月儿心里竟还隐藏着这么一个苦不堪言的秘密。巧红也不知道,巧红只知道月儿有一个和睦的家庭,有一个勤奋老实的男人,有一个伶俐听话的儿子。
这一夜月儿在炕上摇起纺棉花车,她不想再并排着头去听巧红说那些让人睡不着觉的话。新生睡着后,巧红也脱的光溜溜地钻进被窝,中条山的人无论男女钻被窝睡觉的时候大多是巧红这样脱得赤条精光一丝儿不挂。
巧红钻进被窝,见月儿还在不停地摇纺着棉花,就欠起身露出一个雪白的膀子和半个跳跳闪闪的奶子,睁着狸猫一样的花眼,满脸上都是困倦,她疑惑说:“月儿姐,干一天活,你身上就不乏?还有心思纺棉花。快脱了衣裳钻被窝睡吧,不然明天又干不动活了,听说明天是往地里担粪,又是一天重活。”
月儿没有往回扭头,手里的棉花车也嗡嗡转着没有停下,只是低低地回说一声:“你先睡,我纺半个线穗疙瘩就睡。”
巧红叹一口气,把头跌在枕头上重又躺下,她那能睡的着,虎堆几天不在跟前,她想的就不行,他们结婚时间不长,年轻人的狂浪劲头还没有过去。平常虎堆在的时候巧红不干上一回那事,是睡不着的。现在男人不在身边,月儿又不肯陪着说话,她那能睡的着觉,她反反侧侧地在被窝里来回滚。滚一阵还不见月儿睡,就赤条条地从被窝里跳出来,蛮横不说理地抢走月儿手上的纺棉花车,嘴里却哀哀求求地说:“人家想和你说说话麻。”
月儿见巧红就这样精光赤条身上不戴一丝线地站在炕上,只好答应和她一起睡。月儿也脱光衣裳钻进被窝,这时候巧红就嘻嘻地笑了,她把枕头往月儿跟前挪靠挪靠,就又酸酸甜甜地说起来,“月儿姐,你现在想不想新生他爸爸?”
月儿噗地一声吹灭灯捻上豆粒一样跳动着的火苗,再把身上的被筒卷紧,才散散淡淡地说:“不想。”
其实她比谁都想,但和巧红的想法不一样。巧红是因为那种事而苦想着男人睡不着觉;月儿却为耀先的冷暖饥寒而担忧,担心他在水库工地上再受到非人的待遇,再受到别人的歧视。受点苦受点累她不担心,她知道耀先是个能吃苦的人,但她不希望在水库工地上人们再把他当成地主的儿子,当成另类去看待。
“你咋就不想自己的男人呢,我都快想疯了,一闭上眼,就想起他雄雄壮壮地爬压在身上的那种美劲。”
巧红的话打断了月儿悠长的思念,使她的心从二十里外的大沟河水库工地回到这黑洞洞的窑炕上。“月儿姐。”
巧红卷着被子使劲往月儿身边挤靠挤靠。月儿就知道她又要说那些让人心跳脸臊睡不着觉的话了。果然,巧红把嘴对在月儿的枕头边悄悄密密地问:“月儿姐,你们最多一黑夜弄过几回?”
月儿心跳起来,匀畅的呼吸也不由地变的急促而又粗重。这是一个月儿根本没能回答的问题,不是羞不羞,而是她根本就没有过那样的夜晚。十多年她只有过短暂急促的一次,而不是一夜有过几次。月儿觉得脸上滚烫滚烫的,幸好把油灯吹灭了,不然巧红看见她脸红了又要惊惊乍乍地叫唤了。
月儿心慌气闷还没有说出话来,巧红把第二句又问过来:“月儿姐,你们最长弄过多长时间?”
月儿再也憋不住了,她在被窝里用拳头捶捣一下巧红,哑哑地骂一声:“憨憨。”
巧红更往这边挤挤,软软地催着:“说呀,咱都是女人,有啥不能说的。你不说我说,我和虎堆最多一黑夜弄过五回。月儿姐,我现在才知道弄那种事全靠咱们女人,男人弄上一回就稀泥一样地软了,就再不行了,但是你要伸手过去给他揉摸上一阵,他就又行了,又硬梆梆地起来了。我们弄的回数不少,就是时间不长,总是刚刚美的想叫,他就出溜了,就不行了。月儿姐你们呢?你们弄的时间肯定长,教教我嘛,月儿姐。”
月儿让巧红说得浑身稀泥一样地软了,全身难受的那里都想用手摸。这样的话再不能往下说了,但憨憨傻傻的巧红还在痴痴迷迷地说着,一点要停的意思都没有……后来月儿就做了一个怪梦,梦见自己体内进去一根东西,又粗又壮的东西。不是耀先的,是吴根才的。她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没有反抗,没有像那年腊月二十九踢郭安屯一样,把吴根才也从自己身上踢下去。就那样光溜溜地仰面朝天躺着,让他顺顺溜溜地进去了,进的那么深那么狠,她就难受地叫起来,叫的时候两只手却还把他粗壮的腰搂抱的紧紧的。再后来就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
月儿做了一个这样的怪梦,就再也睡不着了。睡不着就听见身边的巧红在梦里嘻嘻地笑,浪浪地叫,她猜想巧红一定也是做了一个类似的梦,但巧红翻动一下身体又熟熟地睡着了。月儿真有些羡慕巧红。
整整一夜几乎没有合眼,第二天起来月儿的脸色就有些难看,就不再是白白粉粉水水秀秀的光彩亮丽了,像是蒙上一层灰土凄凄戚戚的样子。而睡了一夜好觉的巧红,雪蛋儿一样白俏的脸上还像往常一样闪耀着生动的光彩。两个精神状态大不一样的女人顾不上抹头洗脸,就应着上工的钟声紧着往皂角树下走。
往地里担粪是最苦重的活。今天恰恰就是往地里担粪。秋收之前庄稼地里没有大桩活,队长就集中全队的男女劳力担粪。山下平川的圈粪是用小平车往地里拉,山上没有那个条件,就只有靠肩膀担挑。把窑圈里起出来的骡马粪先担倒在地边堆积起来,等秋庄稼一收腾出地,往里面拖撒就方便了。
月儿和巧红从坡道上下来,吴根才已经在皂角树下向社员们派开活了,除各别几个人被派去干零星活,剩下的人不论男女都担挑着篓子去窑圈担粪。月儿巧红相跟着下来,肩上都担着空粪篓刚要往窑圈那边拐,政治队长郭安屯突然把巧红叫住,月儿也同时回过头,看见叫住巧红的郭安屯正低着头和吴根才商量着什么,而吴根才似乎并不在认真地听他说,而是睁着大眼直直地盯在自己脸上看,月儿忽悠一下就想起夜黑间做下的那个荒唐的怪梦,马上就一脸的羞红,垂下脸扭过身走了。巧红不敢走,因为政治队长把她喊住,还没有吩咐出别的话呢。
月儿担着两个空粪篓走了之后,吴根才才听清郭安屯在给他说啥。郭安屯的意思是:上河滩地里的三十亩谷子快熟了,快熟的谷子最怕山雀儿祸害,得派一个人过去吆赶山雀。吴根才就答应说:“那就派一个人过去吧。”
郭安屯马上转脸对等在一边的巧红说:“巧红,你到上河滩三十亩谷地吆山雀看谷子去。”
吴根才脖子上粗大的喉节骨嚅动着却没说出话,他没想到郭安屯会安排巧红去看谷子。照理说吴根才是卧马沟的生产队长兼党小组长,是一把手,政治队长郭安屯和副队长李丁民是协助他工作的。指派谁干啥是他吴根才说了算的,可眼下郭安屯越俎代庖偏偏这样安排了巧红。吴根才想想还是没有说啥,政治队长和副队长也有安排社员干活的权利。
巧红担挑着空粪篓往下走的时候还撅着嘴给月儿嘟嘟囔囔地说又是一天担粪的苦差事。担粪对身强体壮的男人们来说都是一项苦重的差事,对月儿巧红这样细皮嫩肉的女人就更苦更重。但巧红的话刚一说完,就让政治队长喊住,接着就派了看谷子吆山雀这样轻巧不出力气的好活。巧红雪蛋儿一样白的脸蛋上当下就喜欢的绽开了花,扔下担粪的空篓子,就欢欢势势地向上河滩的三十亩谷地跑去。
圈粪是往下河滩的玉茭地边担,三十亩谷地是在上河滩。所以月儿并不知道巧红被政治队长叫走干啥活去了。月儿几乎一整夜没有合眼,但她还得一趟不少地担着圈粪往地里送。世道不公平,男女同工不同酬。这种不公道在月儿身上表现的尤为突出,月儿一天只挣六分工,却要和那些一天挣十分工的男劳力们干一样的活。队里规定一个人一晌担八担,谁担完谁歇,担不够不给记工。这样的规定是把虎林那些好偷奸耍滑的人给治了,同时也把月儿这样柔弱的女人给坑了。
强壮的男人和有力气的女人担挑着粪担都抢着道往前去了,谁担完谁歇,人们争前恐后都想早一点把自己的八趟担完,早一点坐到树荫里去歇。身体单薄的月儿落在最后,有些人六七担都担送到地里了,都四仰八叉地躺在皂角树下歇上了,月儿肩上的第三担还吭吭哧哧地没送到地里。吴根才担挑着一担粪从后面赶上来,他本来可以轻轻松松地过前面的月儿,但他没有。河渠上担粪的人拉开距离就显得稀少,再加上有些人快把自己的份额担完,都歇在皂角树下了,河渠上的人就更显的稀少。吴根才担挑着粪担儿悠悠地跟在月儿身后,想和她扯说上几句话,凡是在没人的时候,他总想看着她白粉俊俏的脸蛋儿和她说几句话,哪怕是闲话哩,他愿意说。他觉得这个女人不仅长的好看,说出来的话也风铃儿一样清清柔柔的好听,这是一个让他见了就心旌摇动的好女人,他也想给她一些关照,可惜她却摊上一个那样的坏成份,他就不好照顾她了。如果让她看谷看场,去干轻松不出力的好活,别人的闲话就多了,惹出闲话不值。唉,这么好看的女人肩上压着这么重的粪担,真让人心疼。吴根才想要说话,却现脸前的月儿走的摇摇晃晃与往日大不一样。往常他也跟在月儿身后担过粪,虽觉的身体瘦弱的月儿担着有些吃力,却也是直往前走的样子。今天晃悠着瘦瘦的身子像是没有了骨头,软软的飘飘的随时要在河渠上跌倒的样子。他就忍不住问一声:“月儿,今天你是咋咧?”
月儿虽然没有回头,但是在河渠拐弯的地方,她就现吴根才在后面担挑着粪担赶上来了。夜黑间一夜没睡着觉,就是因为他呀。那个荒唐的怪梦就和真真切切生过一样,她梦见他的东西进到自己的身体里,接着就有了那种说不上来的要死要活要飞天成仙的感觉。由于那个荒唐的怪梦在心里作出祟,也因为真的没有休息好,当现吴根才跟在身后的时候,好像真的和他有过那种事情一样,月儿在前面就紧张慌乱羞臊的迈不开步,走不动路,腰是软的腿是抖的,眼里看人也是恍恍忽忽的两个重影。吴根才再低声关切地这么问一声,月儿就真的坚持不住了,她把担子一放,扭过脸给吴根才让出道儿,他要是这样一直跟在身后,她就把这担粪送不到地里去了。月儿歇下担儿让开道,吴根才却没有马上越过去,他把担子也歇下来,因为他看见月儿的脸色不对劲。在卧马沟恐怕再没有谁比他更关注月儿的脸了,他常常把火辣辣的目光直勾勾地盯在她脸上看,他每次在她脸上看到的都是白白粉粉桃花一样鲜亮醉人的美丽。可是,今天她的脸却惨白的像是一张粉联纸,那红粉粉鲜美醉人的颜色那里去了?吴根才放下担子,他自己的大脸盘上先有了不小的惊诧,急切地问:“月儿你究底是怎么啦?是不是病啦?脸上咋没有一点点颜色?”
月儿羞涩的不敢往起抬脸,他的急切,他的关心,使她又一次想起个荒唐的怪梦,那是一个逼真如实的荒唐怪梦,那是一个害的她一夜睡不着觉的荒唐怪梦。月儿不吭声也不往起抬脸,吴根才就更有些焦虑,他说:“月儿,你要是真的身上难过,就不要强担,你在这歇着,等着我回头来接你的担子。”
他说着担挑起粪担急匆匆地前去了。吴根才走后,月儿就扬起脸,在她惨白失色的脸上又多了一层从来没有过的复杂的表情。
等吴根才在粪堆上放下担子,倒掉粪篓里的圈粪,准备回头去接月儿的担子时,月儿也就晃晃悠悠地到了粪堆旁了。吴根才还是跑过来接了她肩上沉沉的粪担,回头看看四下没人,就对站在粪堆上手里握着铁锨,连平堆带记数的记工员喜娃说:“喜娃,给月儿多记两担粪,她今天身上不好的难过哩。”
喜娃见旁边再没有人,就笑着向队长点点头。对耀先月儿,喜娃一向也是同情的,他乐意接受队长的这个命令。
月儿明白了自己夜黑间为什么会做出那样一个怪梦,明白了为什么自己在梦里会是那样的表现,会顺顺溜溜不做反抗地让他进去,因为……月儿不敢再往下想,担起空担羞羞地走了。
郭安屯只往下河滩地里送了一担粪,就撂下粪担背抄着双手到别处查看去了。做为政治队长,他有权随时到别的地块去查看监督。
郭安屯转过身刚走远,坐在皂角树下的虎林就阴怪讽刺地说出一句新编顺口溜:“奸的转,精的看,傻的干。”
社员们一阵哄笑便再不能说啥,说啥呢?谁能管得了政治队长。
现在的吴虎林早已不是原先的那个吴虎林了。现在的虎林变的奸滑懒惰油泥散漫,简直成了生产队里的刺头儿。谁拿他也没办法,谁也不爱见他。一个人的变化竟然会这样大,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有人说是入社时让郭安屯一绳子给绑的。也许那是个原因。四十里马沟三十二村,只有吴虎林一人是用绳子绑进农业社的,强扭的瓜不甜,除此之外是不是还有别的原因,肯定还有,只是暂时人们看不出来说不出来罢了。
郭安屯撂下肩上的粪担儿背抄着双手,昂阔步到别的几块田地里查看庄稼青苗去了,他是政治队长有这种权力和责任。虎林的顺口溜编说的再好也是白说。郭安屯像模像样地查看了几块庄稼,一扭身就沿着河渠向上河滩的三十亩谷地去了。
把虎堆打着修水库走了之后,郭安屯就急切地想要对长的像雪蛋儿一样白白嫩嫩的巧红下手。巧红现在对郭安屯有着极大的诱惑,就像原来的月儿一样,他一想起巧红就走不动路,下面裤裆里的东西就蓬蓬勃勃地往起鼓胀,就想弄那种事。确切地说,就是那次在后沟割草他才开始真正注意上巧红的,在那之前,他心里一直想的还是月儿。在后沟这个巧红闪着狸猫一样的花眼不断地和他调笑,他的心就咯噔一下动了。细一端详巧红长的也不比月儿有多差,于是就对巧红下起功夫。巧红和月儿不同,巧红身上干干净净的没有背负任何政治上的污点,她还有个年轻二旦的男人,对巧红只能用引诱的手段慢慢来,对巧红使用硬手段是不合适的。硬手段只能在月儿身上使。经过一段时间的试探、引诱和挑逗,郭安屯就现巧红和月儿大有不同,月儿软硬不吃,这个巧红你只要一挑逗,她就和你眨闪眼睛,好上手的很。大沟河修水库让郭安屯逮住机会,他觉得只要把她男人虎堆远远地支走,她就会像河渠里的水顺顺溜溜的听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