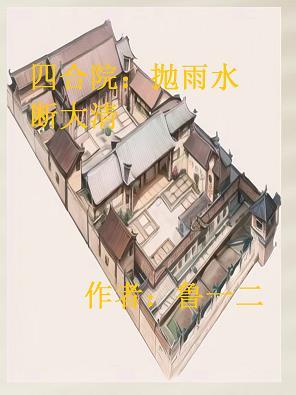69书吧>和肖邦弹风谱月的日子格格党 > 第1章 EtudeOp 1(第4页)
第1章 EtudeOp 1(第4页)
“这都要怪你,我的夫人,你一年到头难得犯糊涂——而你却做了此生你最蠢的许诺。要不是我提早说见一见那个孩子,咱们就要背信弃义令家族蒙羞啦!”
“老爷,可咱们不一定要‘牺牲’这个女孩子。我是说,我们可以找个借口冷处理那个许诺……”
自家夫人天真的心软简直令男人觉得不可思议。
“牺牲?冷处理?我的夫人,呆在德累斯顿让你的脑子变迟钝了?我们能收留那个孩子是出于仁义——难道最大的仁义不就是给她找个可靠的夫家吗?我们看着长大的男孩子人品是可靠的,在巴黎也能挣上钱,不会委屈她。”
“那为什么你不愿顺势而为呢?肖宾斯基[5]应该指的是玛利亚。哦,上帝啊,我们这是在欺骗那个天使一样的孩子……”
“还要犯傻吗,我的夫人?我们的玛利亚注定是要当伯爵夫人的,怎么可以停留在他身边——听着,夫人,我也很喜欢他——但喜欢不能换来你的衣食和优渥。沃德辛斯基已经没落了,天使救不了我们!”
伯爵夫人想起那个棕蓝眼的优雅青年,流亡在法国却永葆着那颗波兰心,又愧疚又难过。
但丈夫的话却字字在理。她不禁开始后悔,如果没有几天前感性的冲动,她此刻也不用连着伤害两个孩子。
“你说服我了,只是我暂时无法释怀内心的感受,去‘安排’那个父母双亡的女孩子……”
“相信我,我也是忍着心痛的。好了夫人,她来了你就好好招待她——我们多给她一些补偿。或者,你可以教教她,如何规避真正的婚姻到来……”
伯爵叹着气敲了敲桌子,但目光却是不容置疑的坚定。
幸好他的夫人还维持着贵族的理智,即使做了口头约定,也未言明是哪一个“女儿”
。
还好,一切还有挽救的办法——他绝对,不会交出他的玛利亚!
德沃辛斯基伯爵捏紧右拳,猛地落向桌上的一封信件。信纸上的波兰文字体清丽秀气,落款写着——
auroraodzinska(欧罗拉·沃德辛斯卡)[6]。
*
车窗外夜色笼罩着一切,清凉的夜风拂过正在奋啃食姜饼的少女的面颊,带走她一身的沉疴。
身体充电完毕,平静下来的欧罗拉着呆,任由车马将她拉向充满迷雾的前方。
直到此刻,她才得空思索如何踏出下一步。
从波兰华沙到德国德累斯顿,从一场郑重的道别跨进未知……少女理应是惶恐不安的。毕竟直到现在,“十九世纪的aurora”
的过去与未来,对她而言是一纸空白。
但这只左手,却隐隐给予她前行的勇气。
既来之则安之——欧罗拉给自己打着气。
毕竟日子还要继续,只希望能像佩蒂特期待的那样,“以后一定好好的”
吧。
……
“德累斯顿到啦。”
马车行驶渐缓,车夫的吆喝伴着铃响将欧罗拉的神游掐断。
心跳不由地加快度,连带着头皮都有些麻。她深吸一口气,摒在胸腔中。紧张从脚下升起,车厢外的未知令她脑中一片空白。
此刻她才后知后觉,下车后,她将彻底融入这个时空。
“只因春日更迭再来,圆月别后重访,花儿年年都返回枝头绽放……
正如我和你道别,是为了再回你身旁。[7]”
茫然间,泰戈尔的诗句在她耳畔回响,竟将那些惶恐与不安慢慢驱逐。欧罗拉怔愣片刻后,随即握住左手笑了。
几小时前,她还在和钢琴道别;现在,她又能驱使双手歌唱。
甚至,她还能遇见青年的音乐大师肖邦。
还有什么可怕的呢?
欧罗拉坐正身体,安然静待车门打开。
1836年,十九世纪的浪漫时代——
你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