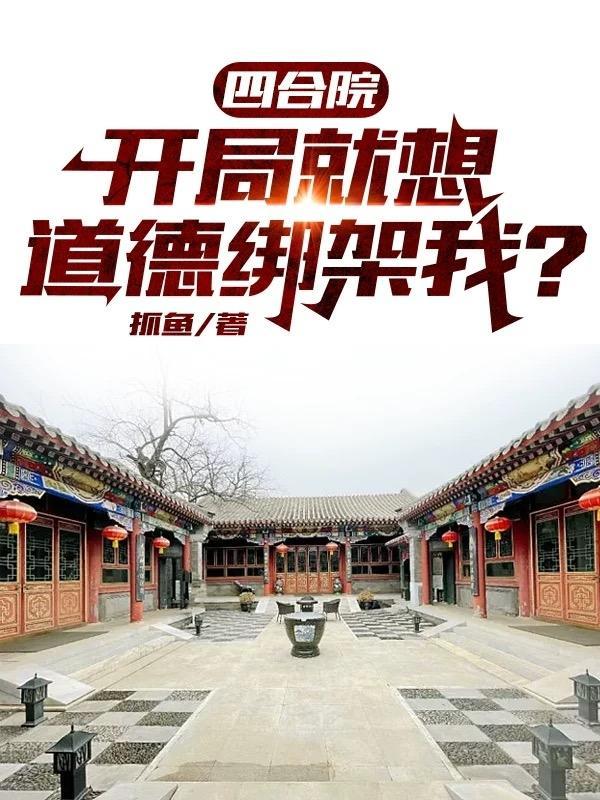69书吧>中国第一个火种的起源 > 第65章 荒诞戏剧(第3页)
第65章 荒诞戏剧(第3页)
说着,大厅暗了下来,就像熄灯的剧院一般安静。唯一的一缕雷光取代了照明,将许多影子打在破碎的穹顶上。导师那瘦长的身影映在中央,对着观众们深鞠一躬。
雷光轰隆着闪烁,将此世最荒诞戏剧的幕布拉开。
……
被雷光照得苍白的穹顶上出现了许多巨大的影子,那是飞翔的巨龙,它们在天空中交织盘旋,三五成群。只是看起来并不亲密,它们对彼此张开大口出嘶吼,紧接着扭打在一起,利爪和尖尾刺入彼此的身体,扯断对方的四肢和双翼;幸存者并不会停下来享受胜利,而是马上投入下一场厮杀。四周全是混战的身影,以及落败凋零的身躯。
龙与龙的战斗永不休止,只有死亡能将他们分离。
“在遥远的太古,人类还未诞生的时代,巨龙们与野兽别无二致。他们的血管中流淌着凶血,随时随地释放着戾气,其他物种无法满足它们战斗的欲望,于是就跟同胞厮杀。每条龙睁开眼就会投入战斗,直到筋疲力尽或战败而死。这样混沌的时光持续了近千年,直到初代火焰之主的诞生。”
导师的声音回荡在大厅里。
穹顶上的画面改变了,一盏小小的灯火亮在山谷里,一条体格瘦小的龙现了它,并且将其吞噬。巨龙的影子在地上抓挠打滚,似乎饱尝痛苦,好在最终适应了这份力量。她的身躯渐渐缩小,化为一个女人的剪影。她擎起双手,巨龙们因她的动作而休战,纷纷落在地上也化作人类的模样。重生的龙类对她虔诚地跪拜,他们牵起彼此的手,开始建立家园,甚至修建房屋,龙族从此走向文明。
“这只幸运的野兽把原初之火据为己有,成为了初代火焰之主,建立了四境世界第二古老的文明。彼时人类文明还处于萌芽阶段,不知他们做出了怎样的决议,以火种在南境创造了独立的空间,就此隐居起来。偶尔也会外出游走,给予其他种族些许指引。”
导师说。
我看到穹顶上身着长袍的龙类男子被手持木棒的人类围在中间,教会了他们生火和研磨。
“这样的时光又持续了千年又千年,火焰之主几经更迭,但只要这条血脉不绝,龙族文明就可以延续。直到两千年前一场变故生,龙族被迫放弃了南境龙脉,前往东境。”
这一段表现得很隐晦,只能看到天上有许多陨石坠落,大地摇晃着崩裂,山谷一分为二,许多巨大的影子在画面上晃来晃去,巨龙们飞舞着逃离。最后,龙脉的大门被缓缓关闭,机关巨人坐在台阶上看着门页轰隆合上。
紧接着人形与龙形的影子在穹顶上飞掠,似乎表现时光飞逝,岁月变迁。直到一位头戴王冠,气质端庄的女人时才停下,她抚摸着自己微微隆起的小腹,显然是怀孕了。
“亲爱的观众们,终于来到了今天的重头戏,请不要眨眼,最精彩的部分即将上演!”
导师的声音异常兴奋。照在穹顶上的也不再是块状的影子而是精致纸人的剪影,就像我在洛国看过的皮影戏。
女人生下了一枚硕大的龙卵,电光将卵照得透亮,薄薄的蛋壳下两个生命在其中安睡。女人的身体每况愈下,常常会显露疲惫,好在这枚卵带来了希望,周遭的人都洋溢着热情的氛围,对女人与卵呵护备至。
不久后一位头戴面具的瘦长男人出现在画面上,他谦卑地对龙众行礼,献上许多药草和典籍,他在宫廷里讲学,很快就受到了许多人的拥护与爱戴。他为女人配置药物,女人受损的身体也得以好转。面具男因此获得龙族的信任,得以常常去看护那枚寄托希望的龙蛋。
他把手按在龙蛋上,细细地摩挲良久;有时还把头贴在上面似乎在低语什么;画面并未直接展现他究竟做了什么,动作甚至称得上温柔。不知为何我却感到阴冷的恶意,不由打了个寒颤。
最终面具男走出去对龙族们说了些什么,从他摇头的姿态和龙族的反应来看是让人失望的消息。不久之后面具男离开了东境。
“我告诉他们由于同一枚卵里的双生子会互相争夺养分,龙类弑杀的凶性在胚芽阶段就会显现,这样生出来的孩子要么身体羸弱,要么血脉不纯,恐怕很难继承火焰之主。但其实是……”
“其实是你动了手脚。”
我咬着牙说,气血和电流涌过,让我的肺部生疼。
“正是!”
导师愉悦地说。“但龙类那样傲慢、自视甚高,怎么会相信一介人类能对他们做什么呢?更何况这个人类自始至终对他们投以善意。好了,嘘,精彩的这才要来呢。”
穹顶上出现了两个小女孩的剪影,她们几乎一模一样,只是妹妹稍显瘦小些,仅仅是剪影就能看出她们如天使一般可爱。她们在宫殿里追逐嬉戏,在花园里搂着彼此安眠,尽管场合不对我却没法控制的心头一暖。
正如导师所说,姐姐的身体羸弱,常常跑几步就气喘吁吁;妹妹则几乎没有才能,她掌握不好火焰,学不会变形,就连书籍文卷都念得磕磕绊绊,负责教导的老师叉着腰呵斥,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模样。
随后,就连身边的大人们对待姐妹俩的态度也异样起来;碍于身份他们无法在明面上展露自己的鄙夷,于是选择漠视她的渴求、轻待她的情感、制止她的游戏、甚至有意制造姐妹之间的隔阂;姐姐被教授政道和学识的时候妹妹就只能在冰冷的宫殿中孤独等待。
再往后,他们连目光都不愿再投在妹妹身上,她成了一枚弃子,一个失败品。他们错开她渴望的视线,却在背后把蔑视加于其身。那些人的皮影相当粗糙,唯有一双刻薄的眼睛栩栩如生。
“他们这样对待两个小女孩?整个龙族都不知道正义怎么写吗?”
雷登惊怒不已。
“正义?他们当然知道。只要把受损的利益与个体联系起来,任何人都会觉得对她施加恶意就是在行使正义,在群体的正义下就连她的存在本身都是一种罪行。世界上再没有比正义更好利用的东西了。”
导师戏谑着。
画面上的女孩常常扑在姐姐的怀里,肩膀抽动着,似乎忍泣忍得很辛苦。不过没有眼泪掉下来,她拼命克制着,似乎在跟自己较真。她不骄傲,只是很倔强。姐姐的手温柔地抚摸着她的头,似乎能把一切忧愁拂去。
但不久之后就连姐姐也失去了。她被戴上王冠,推到高高在上的王座上,人民在她脚下欢呼,亲吻她的手背。民众的愿望等待她去回应,姐妹相见的时间越来越少。画面上,妹妹的剪影在宫殿中徘徊得越来越久,有时她会独自坐在镜子前,一坐就是一整天。
穹顶上满溢而出的孤独刺得我心里很疼,以至于面具男出现在妹妹身边时我的第一反应居然是松了口气。
他似乎回来有段时间了,但却是第一次与妹妹相见。他是姐姐的药理学老师,也会为她讲解许多人类社会的故事与见闻。妹妹不被允许听他的课,他也不被允许与妹妹接触,但他仍会悄悄溜出来,带着姐姐与妹妹相聚。
三个人在狭小的密室里席地而坐,他的脑袋中装着永远说不完的故事,他身上有种莫名的亲和力,仅仅是坐在他身边就会觉得温暖。身为学者,他身上却没有半点呆板的样子,即使是鸡毛蒜皮的小事也会被他讲述成动人的故事。在无数个深夜,姐妹俩都依偎着聆听那些故事,直到不甘心地睡着。
他的态度不卑不亢,不高看她们也不轻贱自己;在这里她们不是女王、不是王储、更不是失败品,只是最普通不过的女孩。这让她们感到莫大的放松。
妹妹不能上他的课,姐姐就转述给她听;姐姐平日为公务操劳,他就为她们泡安神解乏的茶;生活中受了委屈,她们就向他诉说,而他也温和地给予安慰。他是她们的老师、朋友、隐藏心事的树洞,由于他是人类她们甚至可以不把他作为长辈看待,所以他也是同龄的玩伴,而同时他又给予她们慈祥的关爱,就像从未谋面的父亲。
与他相处的那几年,是她们一生中唯一被当做孩子对待的时光。柔和的白光跟随着他,将他周边的世界照得亮,是他带来了光还是光带来了他,我分不清。
“你为什么要回去?”
我按着因为心跳而越疼痛的胸口,沙哑的问:“你要是想践踏陶雅的精神,让她觉得自己只是个没用的灾星就该放任自流,为什么要再给她们希望?”
“你会觉得踩地上的蚂蚁很有趣吗?要是不保留一点反抗的意识和尊严那怎么会有摧残的快感呢?”